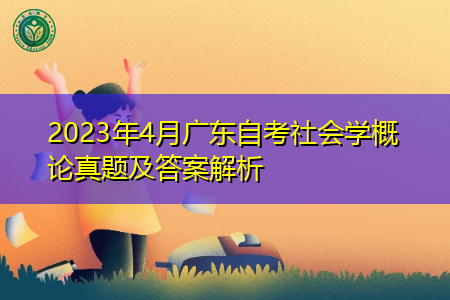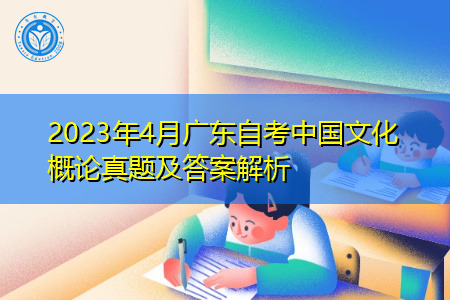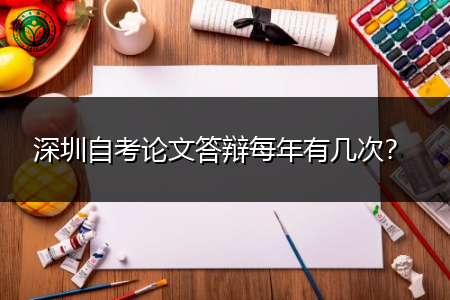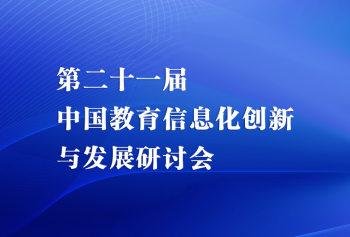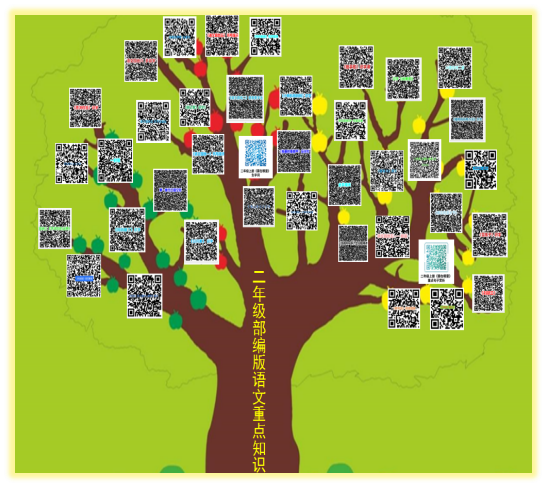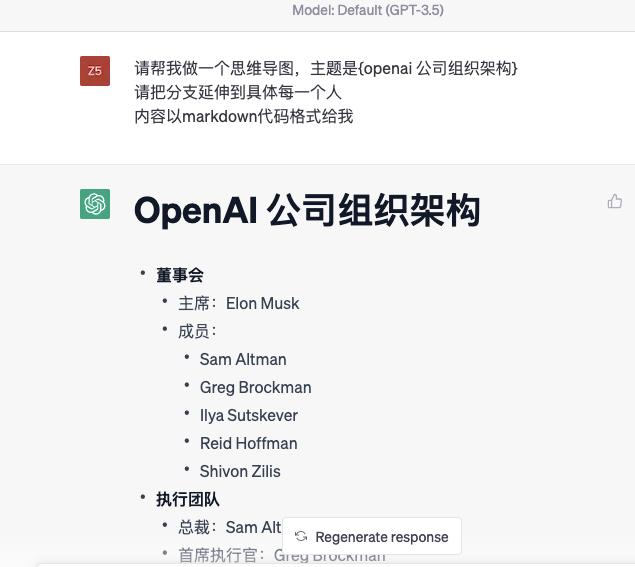摘 要:STEM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之初,就以跨学科整合性作为共同的核心理念。植根于不同文化、哲学、认知论的传统,美国、法国、新加坡三国发展出多元化优势探究系统,并在21世纪核心素养多层次目标的定向下,派生出三维教学、大概念探究性学习、设计思维赋能项目工作三种典型的实践模式。在培养跨学科能力方面,项目化学习和问题化学习作为支撑不同STEM教育实践模式的两大主流教学法,各有优势,也面临不同挑战。三个国家分别用以问题化学习为支架的项目化学习、论证式科学教学、以项目化学习为支架的问题化学习予以回应。基于此,文章初步提出STEM教育的目的—教学法—探究系统三维实践模型。
关键词:STEM教育;跨学科整合性;探究性科学教学;问题化学习;项目化学习;PPI实践模型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方兆玉,法国巴黎高等科学技术与经济商业学院教育管理博士(巴黎 75015)、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教育》编辑部编辑(上海200032)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一般课题“基础教育核心素养培育导向下教师跨学科能力建设及评价研究”(编号:BHA230151)
2023年11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2届大会通过在中国上海设立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机构(UNESCO IISTEM)的决议,标志着教科文组织一类机构首次落户中国。[1]这不但引发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广泛热议和高度关注,也显著提升了社会大众对STEM教育的兴趣,更促使我们对这种创新教育模式进行深度解构与学理探析。
21世纪全球化时代,指向创新能力培养的科学教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我国近年来也推出科学教育相关政策举措。2023年5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推动科学教育各项措施全面落地[2];7月26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首批试点支持30所“双一流”建设高校承担培养任务,遴选理工科优秀毕业生,为中小学培养一批研究生层次高素质科学类课程教师。[3]
STEM以跨学科、跨领域、整合性方式推进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培养学生21世纪核心素养的主要创新教育模式,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首倡至今的20多年间,已经得到英国、法国、德国、芬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教育发达国家的普遍认可和大力推动,并由此催生出共同理念下多元路径、多层次目标定向的实践模式。在如今这个核心素养教育改革时代,重新审视、厘定STEM教育的核心理念和主要目标,并对比三个代表性国家差异化的实践模式,不仅能为我国STEM教育带来多方面借鉴,也有助于研制适合本土情境的推进策略、开发实践模型,切实服务新时代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一、共同的核心理念:跨学科整合性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首次提出STEM概念[4],美国STEM工作组报告中称其为“集结科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数学家力量的一个战略性决定”[5]。STEM强调的是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深度融合,其核心特征是基于各学科核心概念理解之上的跨学科整合性。
(一)跨学科能力
在西方世界,由古希腊滥觞的博雅教育关注“培养整全人格”,主张学科和知识领域的一体性(unity)。近代启蒙运动引发了知识的“科学化”和科学的“职业化”,从而促进了知识的快速生产、传播以及学科化、专业化。[6]然而,正如著名的跨学科学者克莱因(Klain)所言:“一直存在一股促进保持、复兴历史上知识整合、一体性传统的推力”[7]。19世纪开始,过度分化的学科开始出现合并、交叉和整合的趋势,跨学科探究(Interdisciplinary Inquiries)开始兴起。
根据克莱因提出的定义,跨学科是一种解决问题、回答问题的手段,这些问题不能通过采用单一方法或单一路径,得以令人满意地解决或回应。[8]为成功地参与跨学科活动,或更好地参与跨学科学习,并能够生成跨学科理解,以及能在未来的跨学科工作情境中拥有良好的表现,学生就需要足够的个人和社会方面的技能,这些能力统称为跨学科能力(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s)。跨学科能力和21世纪技能高度相关,包括对学科的局限性采取批判性视角、跨越多个学科解决复杂问题、跨学科交流、在跨学科团队中进行合作并具有团队意识,以及发挥学科整合的潜能、提出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方案。[9]
不管是知识学习、职业发展还是服务社会,跨学科能力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在知识学习方面,跨学科提倡对知识和理论发展的整体观。在职业发展方面,企业组织结构越来越往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未来工作场所的项目和任务会越来越复杂,涉及各个不同的专业和知识领域。[10]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创始、致力于在生物基质上创造科技艺术品的美国公司奥克斯曼(OXMAN)的员工就包括计算机科学家、机器人工程师、生物学家、艺术家。正如克莱因所言,跨学科与创新高度相关。[11]创始人奥克斯曼在访谈中提到,“当把科学研究领域的持久性、本质性大问题与最前沿的技术相结合时,就是创新涌现之所”。
而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需要学生超越个人和地方性意识,以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能力和素养去应对全球层面的大挑战,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提出社会性科学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以及创新性产品设计。例如,今天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气候变化、国际关系、深空探索、数智化转型等多重挑战和变革都亟需跨学科人才。又如,奥克斯曼公司的产品既巧妙利用大自然的造化之功,又深刻体现科技的雕塑之力,并凸显人文关怀和艺术美感,以及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这都需要跨越学科领域、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的人才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二)作为跨学科学习的STEM教育
跨学科学习被界定为“一个学习者整合来自两个或更多学科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视角、概念以及理论,以一种单学科路径无法达到的方式去创造产品、解释现象、解决问题的课程教学取向”[12]。作为跨学科学习的STEM教育,正如这一概念被提出时的初衷,“跨界”(boundary crossing)或者说跨学科整合性是STEM教育最显著的特征,虽然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学段以及不同的课程计划对于跨学科整合的尺度把握颇为悬殊。[13]关于跨学科整合性,哈尼等学者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在一个复杂的现象或情境中,要求学生利用来自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来完成任务”[14]。瓦斯奎兹则为STEM的跨学科整合性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按照STEM子学科整合性从低到高的程度分布在一条连续的线上,从左到右学科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逐渐加深。[15]
从各国在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各个学段实际的推进策略来看,STEM教育的实施模式相对宽泛,涉及从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到超学科的多条路径。而美国近些年来越来越重视STEM教育的跨学科和超学科整合,如加州教育部STEM任务组就在其2014年的报告中提出:STEM教育不只是所属四个子学科之间“方便的整合”,而是采用连贯的、主动性的教与学,引入植根真实世界的问题化学习来将学科进行深度连接;此外,这几门学科不能也不应当被孤立地传授,就像它们在现实生活或工作场所中也是一体的一样。[16]
(三)回应跨学科整合度不高、部分学科被弱化的挑战
虽然跨学科整合性是STEM教育的核心要义,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遭遇跨学科整合度不高、某些学科代表性不足乃至被忽视的双重困境。例如,多项纵向跟踪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的数学抽象、建模、推理能力以及工程设计思维、工程设计实践都没能在整合性、跨学科的STEM课程当中得到有效提高。霍奇兰德(Hoachlander)也重申了如上忧虑,“尽管教育实践者、企业雇主、政策制定者十几年来一再强调跨学科整合的重要性,但在大多数美国中小学,科学和数学课还是独立教授的,而工程学科则是缺位的”。[17]
对此,美国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就提出:“推进STEM教育的跨学科整合性,必须同步提升所有四个学科的能见度,必须对各学科的核心内容以及跨学科整合性的概念理解等量齐观。”[18]纵观全球,那些既在国际教育评价项目中交出亮眼成绩单又在推动STEM教育方面成效显著的国家就是例证,如新加坡和芬兰,其成功经验就是既强调学科核心知识,又注重过程探究、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培养。基于此,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建议在推进STEM教育时,向这些国家学习,大力推行同时培育通用能力、强化学科概念以及提升跨学科整合能力的创新教育实践。
对跨学科整合度不高、部分学科被弱化的挑战更直接、更充分的回应来自2013年美国出台的全国性课程标准《下一代科学教育标准》(Next Generation Science Standard,NGSS)。研制NGSS的阵容十分强大,多名诺贝尔奖得主深度参与,经过长时间系统规范、基于教育研究、对标学术标准的研发,NGSS对科学、技术、工程进行全新阐述,成为世界各国衡量STEM教育及其成效的通用标尺或参考框架。NGSS不仅直面数学和工程学科在STEM教育当中遭到边缘化的问题,强调对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量齐观,而且提升了跨学科整合的丰富性,在科学和工程实践部分融入数学思维,其界定的七个跨学科大概念中也包含“数量、比例和尺度”这个数学学科领域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跨学科大概念、学科核心概念和科学与工程实践(三维教学)的强调,NGSS还在强化科学教育(地球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子学科)与数学教育的跨学科横向整合的同时,凸显了科学探究、工程设计与技术产品从理论、实践到应用的纵向整合。[19]
二、多层次目标定向:探究系统、文化渊源与实践模式
最能体现STEM教育核心特征的两个关键词是探究式学习和21世纪核心素养目标。首先,对于大多数教育发达国家来说,从讲授式教学到探究式学习带来了颠覆性的转变,意味着学生而非教师成为整个教育过程的主体,问题而非学科知识成为驱动教育过程的核心力量,动态开放而非预制结构成为教与学的主要组织方式。讲授式教学与探究式学习的主要区别如表1所示。不同国家的主导性探究系统深刻影响了其STEM教育的实施路径。培养目标从学科取向、知识取向转型为能力取向、素养取向的过程中,亦与各国的文化传承、价值观等相互交织,增加了复杂性和多样性。
表1 讲授式教学与探究式学习的主要区别

(一)五种主要的探究系统导向
支撑探究式学习的是在西方现代科学史乃至认知论传统中拥有深厚渊源、占据重要地位的探究系统(Inquiry System)。任何一门正式的学科都自己独特的学科观念、学科视角,以独特的探究方式去获得本学科具有框架性、统领性作用的原则、概念、理论。
美国学者伊安·I.米特洛夫(Ian I. Mitroff)和罗尔夫米·H.克尔曼(Ralph H. Kilmann)将探究系统划分为五大类。[20]第一类是洛克主义(Lockean IS),也被称为实证主义,这类探究系统主张真理是经验性的,经验证据具有不可超越的效度,能作为论据或行动依据的只能是感知、观察或从实验取得的数据或信息,没有任何先验性或必须遵守的理论或解释框架存在。实证主义适合研究结构良好的问题,典型的应用是自然科学实验和德尔菲法。前者依靠控制实验条件下的因果关系解释科学现象或验证假设,而后者则对界定清晰的问题进行维度和层级划分,并就此进行预测,只需在有限的专家人群当中达到一致意见即可。
第二类探究系统是莱布尼兹主义(Leibnizian IS),也称形式主义,这类探究系统认为真理是纯粹分析性的,具有某种理论框架或形式内的逻辑自洽性与完整性。因为莱布尼兹主义者认为所有经验现象都能由其背后的理论框架加以解释,因此,主张对现实数据进行数学的或符号的建模,并提取底层参数,在此之上进行推论和演绎。形式主义在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例如,黑洞就是通过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预测、推断出来的。它符合的是数学公式的逻辑,其经验证据在多年之后才通过天文观测仪器真正捕获到。
一般而言,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都比较擅长处理结构良好、一般意义上比较“驯服”的问题。实证主义可用在探索性的研究领域,通过扎根理论,从现场提取经验数据,其后借助归纳总结得出一般规律或共识;而形式主义则擅长处理抽象的符号系统,探索自然科学的一般性原理。
第三类探究系统是康德主义(Kantian IS), 也被称为多元模式。撰写过《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康德对人类的理性和实践能力都抱有怀疑态度,因而主张在我们试图作出明智判断或科学论述时,应兼采实证数据和理论推导之长,互相补充。康德主义者接受由于经验证据和上位理论匹配的多样性,同一个问题或现象具有多元路径和多个解决方案。很多政策研究、管理研究、教育研究就是采取了这条路径。既需要依照上位的目标系统推导可用策略集和路线图,也需要通过扎根的方式进行问卷调研、结构化访谈以获取目标用户的第一手数据来对策略、路线进行精炼、聚焦、调整和优化。
第四类探究系统为黑格尔主义(Hegelian IS),也被称为辩证主义。黑格尔主义者认为真理是冲突性的,同一现象或同一组数据背后可能可以用若干相互冲突、竞争性的分析或解释框架来进行认识。唯一求真的方式就是把它们都一一列举出来,探明支撑不同解释框架的理论基础,再进行去伪存真、求同存异的合并提炼,得到承认异见基础上的创造性整合(Creative Synthesis)。黑格尔主义探究系统的优势在于解决冲突性议题,如目前理论物理界对于世界的本源就存在几种相互竞争的学说,弦理论、量子场论、隐藏的变量、多重宇宙分别都有自己的拥趸,每种学说都能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作为主导性的解释框架。
第五类探究系统为桑格尔主义(Singerian IS),也被称为实用主义。源自当代哲学家、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的实用主义哲学思路。它不承认解释一切的理论框架,或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客观经验,而只认可特定问题情境下有用的理论或数据,及其对问题主体的效用、美学或伦理价值。因此,桑格尔主义者选用的分析框架是有目的的(Teleological)。[21]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实用主义是一个元探究系统,可统辖前述四种探究系统,并灵活调用、适配组合,只要契合探究目的即可。它对于解决很多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性议题或道德两难问题都具有很高的效度,在追求地方性、情境性知识的同时促进跨学科、开放性、无止境的探究。
总体而言,五类探究系统都有自己的优势,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适合结构良好的问题,而多元模式、辩证主义、实用主义则擅长解决复杂的劣构问题。应用层面来看,各国由于文化、哲学、社会、历史根源,而生长出了不同的优势探究系统(本文以三个典型国家为例加以说明),在差异化的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目标的统领下,衍生出多种典型的STEM教育实践模式。
(二)差异化目标定向下的三种典型STEM教育实践模式
虽然处在同一个21世纪核心素养教育改革的场域,美国注重的是其服务于21世纪职场需要的功能;法国锚定的目标是“实现成功生活并发展健全社会”;新加坡则在其21世纪核心素养与学生学习成果框架中将核心价值观置于中心位置。[22]
2007年,一份卡耐基报告将美国社会的注意力引向科学教育,报告的主要观点是:国家的创新能力、经济发展的动力、本国劳动力的全球竞争力均有赖于优质的科学教育。但可惜国际教育评价项目的测评结果证明,美国基础教育落后了。此后,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临危受命,开始编制共通性、高标准的NGSS。围绕服务经济发展的宏大目标,作为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占据主流话语体系的国家,美国自然而然将实用主义作为主导性的探究系统,从而促使其在STEM教育中从科学探究式转向同时关注理论和实践的三维教学,以服务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支撑STEM产业、提高全民的科技素养的多重目标。
“博洛尼亚进程”中的法国既具有欧洲重思辨、重智识的文化烙印,又希望借助欧盟增强自身的经济力量、提高社会凝聚力。在个人发展与社会经济进步的综合性目标定向下,法国从21世纪初开始在初中科学学科推进名为“发现之路”的跨学科学习计划。2010年,法国开始采用跨学科主题教学模式开展化学、物理等课程。2022年开始,法国国民教育部专门推出“高中科学与数学整合性教学计划”。对于该计划,法国学校教育总干事爱德华·戈弗雷提出的目标引人深思:提供学生需要的数学知识与技能,体验科学探究乐趣,发展逻辑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以及创造力,能运用理论阐述复杂的科学现象。基于此,将科学和数学整合路线设计为“以知识为核心”“以观念为核心”“以问题为核心”的渐进式结构。“人体的热平衡”“生物多样性及其演变”等“知识”指向科学学科的大概念;“能源发展选择”“音乐与数字的艺术”等“观念”明显指向伦理、美学与可持续发展;“人口统计学模型”“声音——需要编码的信息”等“问题”则体现了基于现实问题、跨越学科疆界构建通用框架或模型的努力。可知,法国提倡大概念统领下的探究式学习(偏向形式主义),这些大概念既包括提升就业力的科学、工程、数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也不乏完满人生与和谐社会所需的哲学、文化、思想等大观念。
新加坡从1997年开始大力推行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提出“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Thinking School, Learning Nation)的口号,关键路径就是推行当时称为创新教育、本质上来看即STEM教育的新学习模式。[23]新加坡以实践创新作为自己以教育改革增强国家竞争力、提升创新指数的主要行动准则,在“尊重、诚信、关爱、抗逆、和谐、负责”价值观的统领下,将创新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兼顾的项目工作(Project Work)作为主要的STEM教育路径,使每个公民都能人尽其才,在自己的“人生项目”中发挥创新效能,从而作为整体助推国家的创新发展。新加坡采用的是模型和数据相互增益的多元模式探究系统。从结果端来看,不仅新加坡的中小学生在PISA、TIMSS当中表现优异,而且国家经济发展和创新指数也出现了质的飞跃。2018年,新加坡全球竞争力指数已经排名前三,创新指数也进入前五。[24]以STEM为主要实现路径的创新教育助推国家发展之功可见一斑。
不同社会、文化、哲学、历史背景的国家,基于各异的主导性探究系统以及对21世纪核心素养的侧重点差异,在跨学科整合性方面出现了明显偏好。他们分别锚定科学探究与工程实践(一般性科学知识和地方性/情境性运用),数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学科之间),科学学习与儿童生活(学校学习与现实生活)等不同的整合靶点,以不同的教育改革路径来迫近素养培养的大目标。
美国为弥补STEM行业的人才缺口,保住自己科技人才的竞争优势,在NGSS中提出了三维教学。三维的第一个维度是“学科核心概念”,第二个维度是“跨学科大概念”,这两个都属于知识层面,本质上是人类在长久的文明发展、科学探究史上所积累的认知性成果,代表了认识自然世界的心智模式和概念框架。但第三个维度“科学和工程实践”是方法,是科学各个子领域在观察、探索这个世界时用到的核心实践,包括科学探究和工程设计。三维教学的整合靶点就是科学知识和地方应用。
法国大概念探究式学习关注的中心是戈弗雷所说的“创造力”“科学探究”“批判性思维”“理论阐述”,整合靶点是学科与学科,期待能激发学生在学科边缘进行第一性原理思考的热情,以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并引领社会和产业界产生颠覆式创新。
注重实践创新的新加坡则在全体中小学生中普及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即“共情—头脑风暴—构思—原型—反馈”。这个“为一个用户精准设计其满意的产品”的思维框架整合的就是学校学习与现实生活。在普通中等教育高级水平课程(A-Level)阶段力推的项目工作既涉及对问题所进行的跨学科分析和研究,又侧重知识应用考查,同时整合学科与学科、学校学习与现实生活。
总之,美国在共通课程标准之下要求其中小学生进行三维教学支持的进阶式、学段衔接的科学建模与工程实践。法国将数学与科学各子学科进行深度整合,衍生出从“知识”“观念”到“问题”的三个层层递进的大概念核心,激励学生在科学原理之上探索哲学、文化、历史等人类根源性的问题。新加坡既注重学生的创新创造力培养,又着力提升他们在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因此大力推行设计思维和项目工作。既让学生在长周期的复杂项目中经历问题分析、概念理解、跨学科整合、探索第一性原理的完整过程,又促使他们将创新想法系统化落实,形成工程设计产品,从而提高项目管理、时间管理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当广义的科学教育进入以解决现实的科学社会性议题、服务于21世纪经济发展、拓展人类科学认知边界的STEM教育阶段,不同国家就分化出多元的探索方式与实现路径,美国、法国、新加坡分别代表三维教学、大概念探究式学习,以及设计思维赋能项目工作三种模式。但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STEM的实现路径进行大类划分,是为了分析和研究之用,并非表明这个国家只采用了一种方式。而是这种方式在该国占据了主导位置或者是该国教育界讨论STEM教育的显话语。
三、跨学科能力培养效能:问题化学习和项目化学习之争
以21世纪核心素养作为统领性目标,以跨学科整合性作为核心理念,美国、法国、新加坡的STEM教育模式孰优孰劣?嵌入在不同社会、文化、哲学情境中的教育模式似乎很难进行横向对比,但其实它们的内核都是目前国际创新教育最主流、最成熟的两种教学法框架——项目化学习(iPjBL)和问题化学习(iPBL),区别只在于具体应用时的主导框架以及两者之间的调配比例。而在作为21世纪技能要素的跨学科能力的培养上项目化学习和问题化学习的效能对比,乃至如何选用、如何适配,一直以来也在世界各国的STEM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一)探究式科学教学的六要素
如前所述,STEM教育的一个关键维度是探究式学习。法国教育科学实验室学者迈克尔·格朗格特(Michel Grangeat)在总结、提炼关键特征的基础之上,于2016年提出探究式科学教学(Inquiry-based Science Teaching,IBST)的六个维度[25]。维度一是问题的起源,即谁提出了问题。科学调查都是从一个问题启动的,是教师还是学生主导尤其重要。维度二是问题的本质。探究问题是完全封闭、学生遵循固定的步骤可以求解的,还是开放性、为学生对步骤和方案留出优化空间的,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维度三是学生在开展探究中的责任。从完全按照教材指令、由教师引导学生完成正式探究的各个步骤,到学生自主设计和开展探究,并对学习成果进行检测,课堂的探究性逐步增强。维度四是学生多样性管理,即如何应对学生不同的知识水平、学习需求和探究意愿。从教师调整任务结构或流程来提高特定学生的参与度,到针对每名学生特定的兴趣和需求,进行客制化探究路径设计,教学法的个性化、差异化水平会逐层上升。维度五是论证的角色。探究水平较低的课堂,教师会协助学生进行观点交流;随着探究度的提高,学生会习得如何思考自己的论证,与同伴的论证相比较,并学会引述理论和证据来加强自己论证的力度和可信度。维度六是教学目标得到显性解释。从教师显性表达对课程的期望达成水平,到学生将其内化为量度自己学习成果的标尺,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检测和交流探究过程中的关键学习成果,其探究性水平不断提升。对照IBST六个维度,可见项目化学习和问题化学习同属于探究式学习,支撑两者的都是建构主义教育观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二)问题化学习与项目化学习异同
项目化学习最早于1921年由克伯屈首次引入,作为项目方法吸引学生参与到有目标的、内心驱动的学习活动中。其后,项目化学习逐渐发展、完善,并被定义为包含两个要素的教学法(pedagogy):一是具有一个用来组织或驱动活动的问题;二是这些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会产生一系列人造物或产品,最后以一个集大成者的终期产品来回应驱动性问题,以此作为项目的高潮活动。[26]
而问题化学习则被定义为“一种课程开发和教学的框架,通过创设模拟的真实情境,提出映射真实世界问题的劣构问题,从而将学生置于问题解决者的主动位置,在提升学生问题解决策略的同时,夯实其学科知识和技能基础”[27]。
两种教学法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学习活动都围绕达成一个小组或班级共享的目标来组织,均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自我导向学习以及合作探究;都为学生提供真实运用知识和技能的机会;都聚焦于开放性问题;都以提升学生的21世纪技能为目标。
至于差异之处,学者们一般认为:问题化学习聚焦于学习本身,而项目化学习注重创造一个产品。[28]更具体而言,两者还存在重理论或重实践,重问题分析或重产品设计,以及重研究过程或重项目管理的区别(见表2)。
表2 问题化学习与项目化学习的区别

当跨学科性加入到问题化学习与项目化学习的比较之中,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应用到项目化学习,其产品设计和制作的过程就涉及多个学科不同信息、数据、技能、工具和视角的综合运用,因而导向创新、有效的产品设计。问题化学习聚焦小组成员之间将来自不同学科或知识领域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和视角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创新性的问题分析与研究视角,从而催生原创性的研究设计和问题解决方案。[29]
但实践过程中,作为复杂情境中复杂技能的学习,两者都存在挑战。项目化学习的挑战在于:驱动性问题是否能促使学生在项目活动和相关概念之间建立联系,学生是否带着概念理解去动手操作,以及他们的项目成果是否能体现深度学习?[30]对此,美国学者巴伦等表示:复杂环境当中学习的复杂性很可能会使学生倾向于遵循确定的步骤,而非带着理解动手操作。例如,他们观察到在一个设计项目当中,教师带领学生做实验、设计运送建筑材料进行水上航行的船只模型,在提升学生兴趣方面收获颇丰。随后,他们也发现学生被活动吸引,而错失了反思和探索科学概念的机会。为此,教师必须在一系列情境中做出权衡:如何使学生一方面积极参与设计活动,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反思;如何将学生真实世界的知识融入进来,同时不会对课程计划产生太大影响;如何维持学生在长期项目中持续学习的兴趣和参与度;如何促使学生对设计操作背后的科学原理进行深入探索。[31]
有鉴于此,巴伦等提出:实施基于项目的课程必须遵循四条重要的设计原则才能保证理解性学习:第一,界定导向深度理解的学习目标;第二,提供学习支架,如嵌入式教学、教学工具以及对比案例库,另外,建议在启动项目之前先实施问题化学习活动;第三,确保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为形成性评价和产品修正提供多次机会;第四,精心设计学生参与结构,确保所有人公平参与,以提升每个人的自主意识。此后,他们对一门几何主题的跨学科项目化课程进行跟踪研究发现,五年级学生从契合上述设计原则的问题化结合项目化学习的课程中获得的学术增益十分显著。[32]而巴伦等人以问题化学习为支架的项目化学习的设计思路在NGSS中也得到继承,使得科学探究、工程设计、技术产品纵向贯通的理念得以落地。
注重科学探究、创新力培养的问题化学习在欧洲国家应用广泛,但其对学生的学术背景、认知能力、跨学科思维提出了较高要求。欧洲学者对大学生项目化学习与问题化学习对跨学科能力提升效果的一项对比研究表明,在跨学科技能、反思行为、学科视角识别三个维度上,问题化学习的效果都更显著,因为问题化学习促使学生对学科概念、工具、数据、理论一次次进行精炼、合并、概括,这个过程促进了他们对学科概念框架的理解,并由此生发创新性的跨学科理解。[33]
如何跨过问题化学习的高门槛获得创新能力培养的收益?法国在其探究式教学中强化了科学论证及其归纳、概括等步骤,为理解抽象大概念做铺垫。而NGSS中对工程学科作用的阐述提供了另一条思路:作为K-12工程教育中主要内容的工程设计与工程思维,并不局限于工程学科,而为STEM子学科之间的整合提供了基础性的流程。[34]前置的问题化活动能加深项目化学习中的概念理解,工程设计活动也有助于科学概念的深度连接。因此,能否在问题化学习的知识应用部分增加设计性、产品性内容,提高学生兴趣的同时也打开跨学科整合的高通道,值得思考。
新加坡的项目工作就是一个范例。项目工作是新加坡A-Level的考试科目。在这门课程的背景陈述中,新加坡教育部表示,项目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在这个动荡、不断变化的世界,学生必须学会如何处理议题,加工第一手的、主题宽泛的信息;他们还必须一起工作,共同完成需要多项复杂性技能的综合任务;也必须学会如何以小组的形式,应用所学完成一个项目。[35]至此还是纯粹的项目化学习描述,但接下来,新加坡教育部又表示:“项目工作是一个跨学科学习经历,旨在为学习者提供整合来自多个学习领域的知识,批判性、创造性地应用在真实生活情境当中的机会”。其学习成果包含四大部分:知识应用、交流、合作、独立学习。并规定每个小组必须在28周内完成任务,建议时长为60~75小时。在这段时间里,小组成员可以共同界定项目聚焦的目标,分析和评估收集的信息,准备口头陈述、提交书面报告以及书面的反思记录。报告评估的标准包括:观点的具体化、概念的生成、概念或观点的分析和评估,以及概念或观点的组织。[36]
批判性、创造性的知识应用,以及概念的生成都离不开问题化学习,结合课程目标、实施细则与评估标准,可以看出,项目工作是以项目化学习为支架的跨学科问题化学习,着眼的是学生跨学科理解以及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
基于如上分析,可知在STEM教育中,21世纪核心素养目标、优势探究系统以及教学法构成了实践模式的重要三极,基于此初步提出目标—教学法—探究系统三维实践模型(见图1)。是单独采用项目化学习、问题化学习,还是互为支架、巧妙“混用”,取决于不同国家差异化的21世纪核心素养目标,以及由特定经济、社会、文化情境决定的探究偏好。

图1 PPI实践模型
参考文献:
[1]央视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在华设立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的决议[EB/OL].(2023-11-10)[2023-11-10].https://news.cctv.com/2023/11/10/ARTIbgoA2wJxyphkA7BhvIU0231110.s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EB/OL].(2023-05-26)[2023-05-29].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305/t20230529_1061835.html?eqid=d4893ef70000c6f6000000036475708d.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实施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EB/OL].(2023-07-26)[2023-07-26].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11/202307/t20230726_ 1070952.html.
[4]LYN D. STEM education K-12: perspectives on integration[J/OL].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M education, 2016(3):3.[2016-03-01].https://DOI 10.1186/s40594-016-0036-1.
[5][16]STEM Task Force Report. Innovate: a blueprin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in California public education[R]. Dublin, California: Californians Dedicated to Education Foundation, 2014.
[6]CLARK B, BUTTON C. Sustainability transdisciplinary education model: interface of arts, science, and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2011, 12(1):41-54.
[7]BERNSTEIN J H. Disciplinarity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in the study of knowledge. Informing Science[J/OL].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 emerging transdiscipline, 2014(17): 241-273. [2014-08-25].http://www.inform.nu/Articles/Vol17/ISJv17p241-273Bernstein0681.pdf.
[8][12]KLEIN J T. Interdisciplinarity: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M].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35.
[9][10][11]KLEIN J T. A platform for a shared discourse of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2006, 5(2): 10-18.
[13][14]HONEY M, PEARSON G, SCHWEINGRUBER A. STEM integration in K-12 education: status, prospects, and an agenda for research[M].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14: 52.
[15]VASQUEZ J. STEM: beyond the acronym[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14(12): 10-16.
[17]HOACHLANDER G. Integrating SET&M[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14(12): 74-78.
[18][19]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2-page[EB/OL].(2011-01-01)[2019-03-02].http://www.p21.org/our-work/p21-framework.
[20][21]LINSTONE H A, TUROF M. The Delphi Method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M]. Boston: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32-40.
[22]刘坚,魏锐,郑琰,等. 5C核心素养:教育创新指南针[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1:22-35.
[23][24]李德威. STEM与创新思维[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3: 3-12.
[25]GRANGEAT M. Dimensions and modalities of inquiry-Based Teaching: Understanding the Variety of Practices[J/OL].Education inquiry, 2016(7):4. [2016-12-05].https://www.tandfonline.com/action/showCitFormats?doi=10.3402%2Fedui.v7.29863
[26]KILPATRICK W H. Dangers and difficulties of the project method and how to overcome them: introductory statement: definition of terms[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1921, 22(4): 283-287.
[27][28]JONASSEN D. Supporting problem solving in PBL[J/OL]. Interdisciplinary iournal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2011,5(2):95-119.[2011-12-27]. https://doi.org/10.7771/1541-5015.1256.
[29][33]BRASSLER M, DETTMERS J. How to enhance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interdisciplinary problem-based learning versus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learning[J].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2017,11(2):2-11.
[30][31][32]BARRON B J S, SCHWARTZ D L, VYE N J, et al. Doing with understanding: lessons from research on problem-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J/OL]. 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1998, 7(3-4): 271-311. [2007-04-16]. https://doi.org/10.1080/10508406 .1998.9672056.
[34][35][36]Singapore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Board. Singapor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Higher 1 (2022) Project Work (Syllabus 8808)[EB/OL]. (2020)[2023-10-02].https://www.seab.gov.sg/docs/default-source/national-examinations/syllabus/alevel/2022syllabus/8808_y22_ sy.pdf.
Competences-oriented STEM Education: Ideas, Goals, and Practice Prototypes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Singapore
FANG Zhaoyu1,2
(1.Institut Supérieur des Sciences, Techniques et Economie Commerciales, Paris 75015, France;
2.Shanghai Education Magazine, Shanghai Educational Press Group,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Upon initiation in the 1990s, STEM education has anchored on the core idea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Singapore, rooted in diversified cultural, philosoph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s, have developed plural dominating inquiry systems, which in turn led to the evolvement of 3D Teaching in the US, Big Ideas-oriented Inquiry Learning in France, and Project Work empowered by Design Thinking in Singapore respectively. Meanwhile,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as the two mainstream frameworks backing STEM education practices, encounter challen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the mixed situations, the three countries had responded in iPjBL scaffolded by iPBL activities, Argumentation-strengthened Science Teaching, and iPBL scaffolded by iPjBL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this paper proposed initially a STEM education practice model featuring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Purpose, Pedagogy and Inquiry System, namely, the PPI Model.
Keywords: STEM Education;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IBST;iPBL;iPjBL;PPI Model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王亭亭
原标题:素养本位的STEM教育:理念、目标与实践模式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4-02-26 12:00:00
时间:2024-02-26 1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