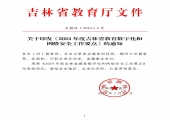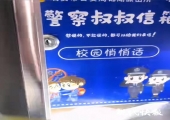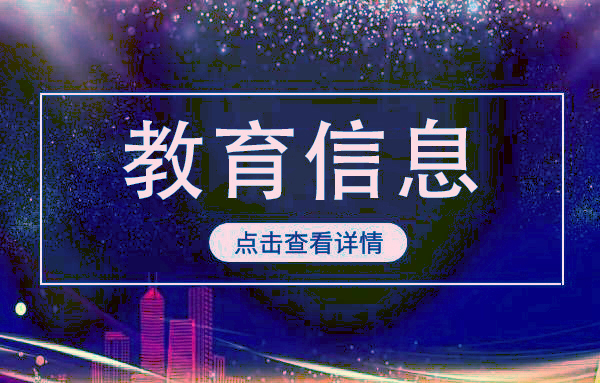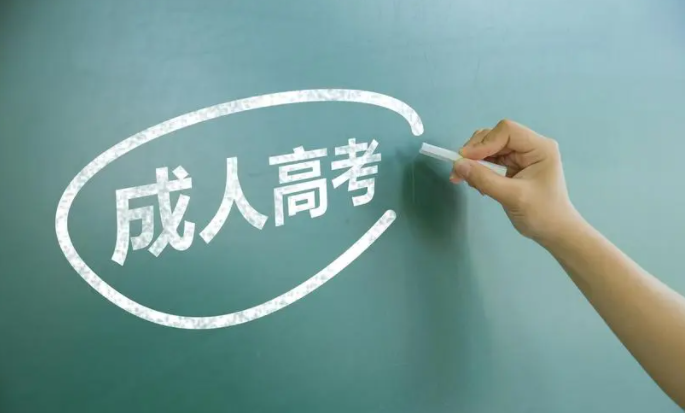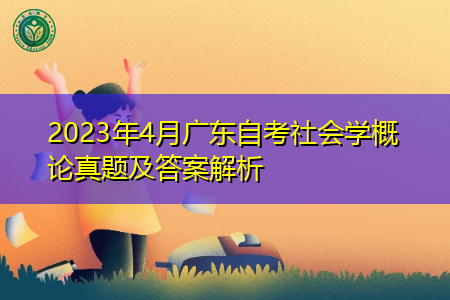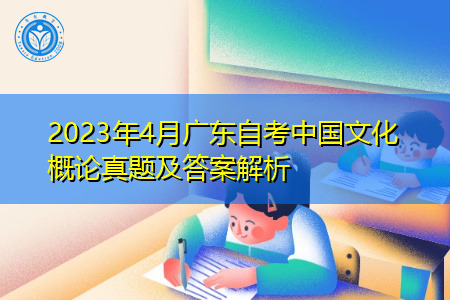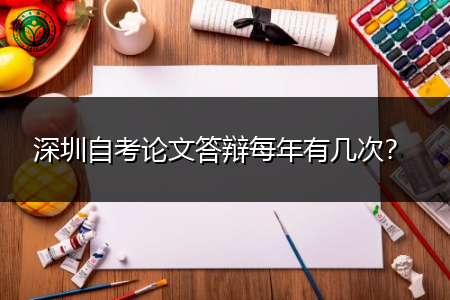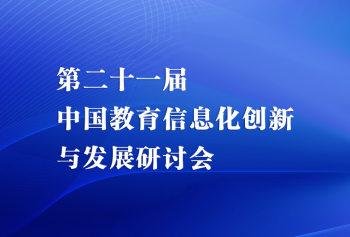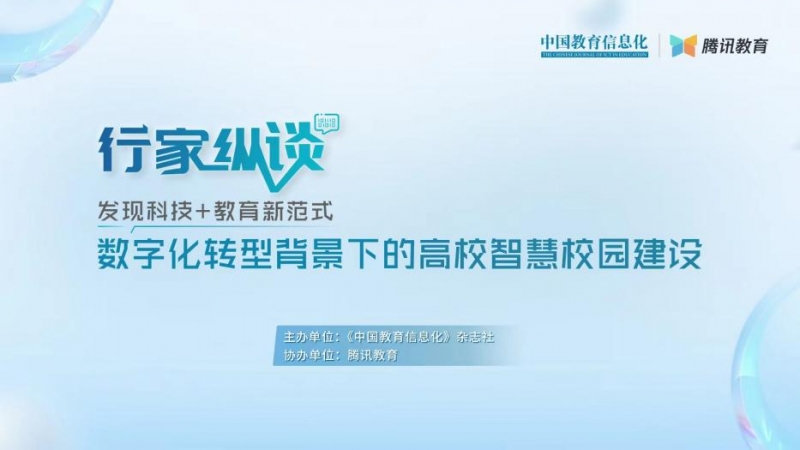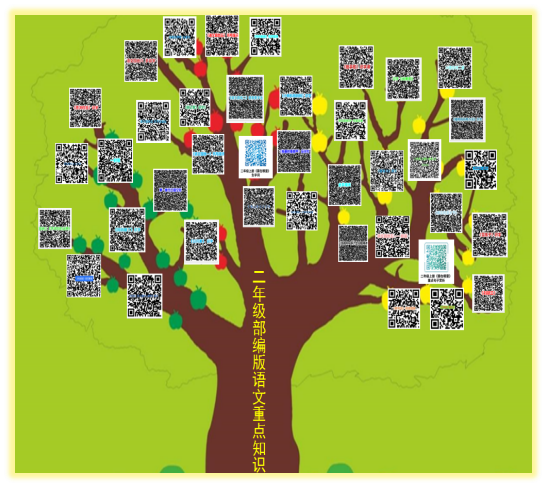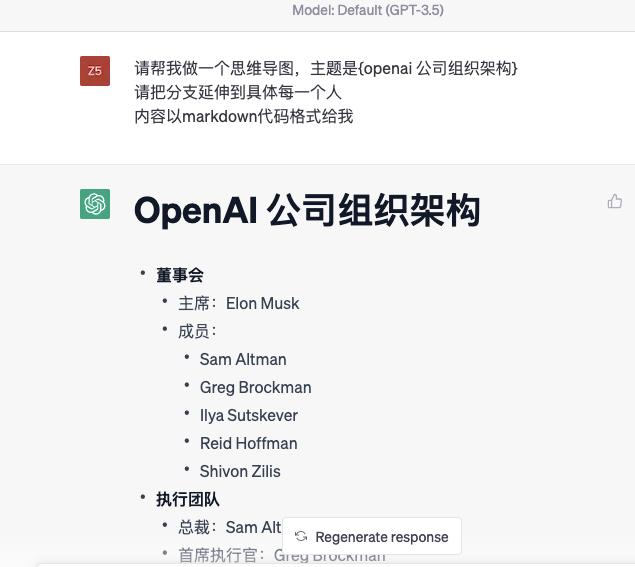摘 要:高校是高层次人才集聚和培养的重要平台。回归以来,澳门高等教育实现了有序快速发展,高校人才队伍总量持续增加,集聚效应开始显现,这主要得益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通过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的双重政策调适,正面引导和优化配置高校人才发展,实现了澳门高等教育从自由发展到目标牵引的转型,澳门人才政策从封闭保守向自信开放的转型。内地高校人才队伍建设中,可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及适度的福利待遇,切实提升高校人才治理水平,严格控制人才认定标准和程序,强化企业的社会公共责任;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中可进一步增强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和提高人才获得感和幸福感。
关键词:澳门特别行政区;高校人才;人才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周江林,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上海 20003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大数据与教育决策实验室”研究人员(上海 20003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双一流’高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机制研究”(编号:BGA220160)
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需要进行战略布局。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集中国家优质资源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家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为人才提供国际一流的创新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1]澳门由于地域狭小人口众多,常被视为“微型社会”,但2021年人类发展指数(HDI)达0.946,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标准,已属于高度发展地区①。
人才和高校人才均是一个具有特指内涵的概念。从人才学的角度来审视,人才是指有特殊才干的人,高校人才则是指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人才。由于澳门高校教师规模不大,科研人员不多,高层次人才更少,因此,本文所说的澳门高校人才与高校教师的外延基本重合。分析澳门高校人才政策的调适有助于寻找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共同规律,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借鉴。
一、回归以来澳门高校人才发展的新变化
澳门是远东地区高等教育的发源地,早在1594年就成立了圣保禄学院。尽管澳门高等教育起步较早,但中断的历史太漫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真正恢复和发展起来。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澳门进入过渡期。为满足澳门中文合法化、公务员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的需要,澳葡当局着手兴办高等教育,为此专门成立澳门基金会,该基金会于1988年2月收购了主要在澳门本地以外招生的东亚大学;1991—1992年,公立东亚大学又一分为三,成立了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大学、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2]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后,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重视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加大了高等教育的投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投身高等教育事业,还更加注重顶层设计,从国家战略高度、世界发展趋势和区域一体化等层面谋划澳门高等教育的中长期发展。澳门高等教育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日趋多元化的新阶段,并逐步形成公立私立并存、分工相对明确、层次类型多样且初具规模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高等教育综合竞争力和整体实力也在稳步提升。相应地,澳门高校人才队伍也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一)高校人才总量增幅明显
1999年回归初期,澳门只有7所高校(分别是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澳门城市大学、圣若瑟大学、澳门镜湖护理学院以及澳门保安部队高等专科学校),1999—2000学年,共有教学人员834人。[3]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赋予其“一中心(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一平台(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一基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重大使命,并将其列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珠江西岸唯一的中心城市。在此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和人才队伍建设。2000年,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管理学院成立;2001年,中西创新学院成立。至此,澳门高校增加到10所。教学人员也在2001—2002学年达到1017人[4],首次突破1000人关口;2009—2010学年再次突破2000人,达2088人[5]。此后十年稳步增加,到2021—2022学年达到2784人。[6]相较回归之际,澳门高校教学人员增加了近2.4倍。
(二)高校人才结构持续优化
回归后,澳门高校人才队伍在学历结构、来源结构等方面都在逐步完善和优化。澳门各高等院校不断改善教学条件,积极从境内外招聘了一批具有博士学位及丰富教学经验的人员任教。[7]数据显示,2011—2019学年,澳门高校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提高近20%,达66.47%。此外,回归前,澳门高校普遍不重视科研,基本上以教学为主。1999—2000学年,澳门高校只有8位科研人员;2010—2011学年也只有47人,占教职人员总数的1.37%。[8]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加大研发投入,以及澳门高校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工程,科研人员的绝对量实现了重大突破:截至2019—2020学年,澳门高校科研人员已经达到623人,占教职人员总数的11.1%。其中,澳门大学的科研人员增量最多,从2010—2011学年的1人,增加到2019—2020学年的372人。[9]
(三)高校人才国际化程度加深
澳门拥有“三文四语”的传统,国际交流的优势明显,被称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摇篮。回归前,这种特殊的优势并未被充分转化为澳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的动能。由于澳葡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忽视以及澳门高等教育自身办学水平和影响力有限,难以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澳门高校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回归以后,随着澳门经济的企稳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高校人才国际化程度日渐加深。以外聘人员为例,2012—2013学年澳门高校的外聘教学人员为657人,2019—2020学年增加到950人。[10]虽然外聘人员仍主要来自亚洲地区,但已覆盖全球其他五大洲,占比由高到低依次是欧洲(6.84%)、北美洲(5.58%)、大洋洲(1.26%)、南美洲(0.53%)和非洲(0.21%)。[11]以澳门科技大学为例,2012—2013学年,该校共有309名外聘教学人员,但来自南美洲和大洋洲的外聘教学人员仍处于空白;2019—2020学年,外聘教学人员增加到380人,不仅填补了上述外聘教学人员来源地的空白,来自欧洲的教学人员也由1人增加到11人。[12]
二、澳门高校人才发展的双重政策调适
国内外的历史实践表明,政策干预和市场机制是两种重要的人才开发手段,其中政策干预是影响人才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合适的政策在促进人才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正面引导和优化配置功能。一般而言,影响高校人才发展的政策往往涉及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以及人才政策等多个方面,教育政策和人才政策对高校人才发展的影响力相对更直接和紧密。
(一)高等教育从自由发展到目标牵引转型
澳葡政府管治期间,政府对其应该承担的教育职责置之不顾。 回归初期,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尚未散去,澳门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重心是推进经济发展、惠及社会民生和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未给予更多关注。2000年3月29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时任行政长官何厚铧在澳门立法会发表的施政报告中,对高等教育的论述并不多,仅提及“政府将完善各高等教育机构的功能及提升高等教育的质素,进一步为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13]。此后,随着经济发展态势的逐步上扬以及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才渐渐加大了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干预。
第一,着手研制澳门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回归后,澳门的社会治安明显改善,社会各界对民生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加关注。为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委托马克·贝磊组建研究团队,对澳门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开展评估,贝磊团队提交了《澳门高等教育新纪元策略性发展咨询研究报告》,从决策过程、成本、融资、素质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2015年,澳门高等教育人员交流协会委托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制《澳门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澳门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提出目标建议,提出将澳门高等教育发展作为新的增长点和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引擎等观点。2020年12月28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澳门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2021—2030)》,作为未来十年发展的框架性、纲领性文件,并提出了建设培育优秀人才的平台、引领学术研究的平台和服务特区发展的平台三个总体目标,明确了八个发展方向:完善机制建设;适度扩大学生规模,优化生源和课程结构;促进院校发展和资源共享;保障高等教育素质持续提升;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强化院校人员专业水平;推动科研创新及产学研发展;把握区域合作机会开拓发展空间等。[14]
第二,强调高等学校的科研功能。回归前,澳门高校基本上是以教学为主,且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在市场化导向下,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这也是导致学生赴外地、外国求学的原因之一。2000年11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何厚铧在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将推动教师重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启发学生参与学术研究的兴趣,亦将支持高等院校成立科研部门,并拓展和私人机构的合作,从而为澳门的发展作出贡献”[15]。此后,澳门相关部门加大了对高校的科研投入力度,也增强了与内地的科研合作。2020年7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任行政长官贺一诚在澳门大学2019—2020学年大学议庭及校董会联席会议上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是澳门高校应有的承担,并认为,澳门大学是澳门高校的“龙头”,必须努力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高校办学功能的完善,尤其是科学研究潜力的挖掘及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代表了其在新时代对澳门高等教育使命的高度重视。截至2024年2月,澳门高校已经拥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批教育部研究中心及基地,聚集了一批世界顶尖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团队。
第三,优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澳葡政府对高等教育缺乏管理,直到1992年才在政府机构中设立高等教育辅助项目组,隶属于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务政务司,负责澳门各大院校的协调工作。在对大学的具体管理中,澳葡政府根据25/92/M号法令,采用行政总监制,行政总监与大学正副校长地位相同,作为大学管理委员会成员之一,负责大学的行政、财政和资产管理,导致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严重丧失。1998年,末任澳门总督颁布11/98/M号法令,取消高等教育辅助项目组,设立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定位为负责辅助、跟进及发展澳门高等教育,并对高等学历进行认可的技术办公室。回归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调整了公立高校的治理架构,采用校监制,特区行政长官为公立高校的校监,在课程设置、国际交流、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赋予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和学术自主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逐渐理顺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于2018年8月设立高等教育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基金会。前者主要代表社会,协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推进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衔接;后者则代表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背景的第三方机构,为高校提供资助及财政援助等。2019年2月,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升格为高等教育局,专责处理澳门地区高等教育事务,监督高校的办学行为,高等教育局直接向社会文化司司长负责。
第四,推进依法治理高等教育。1991年,澳葡政府颁布《关于订定在澳门地区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一切公立及私立教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即11/91/M号法令,这也是澳门历史上第一部高等教育制度框架,成为澳葡政府管治澳门高等教育的纲要性法律,奠定了澳门高等教育治理的基本法理逻辑。回归后,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澳门又新增了三所高校,高等教育发展日益受制于回归前遗留下来的法律,跟不上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2002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为此进行了检讨,并于2003年拟定新的《高等教育制度》行政法规草案,但未进入立法会修法程序。2014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再次讨论了该行政法规草案,从教育素质保证、高等院校管理、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教育资助六个方面提出修订建议。2015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通过该行政法规草案;2017年以第10/2017号行政法规正式颁布,正式取代原有的第11/91/M号法令,将澳门依法治教推上新的阶段。此后,澳门又分别颁布若干行政法规,如《高等教育素质评鉴制度》(第17/2018号行政法规)、《高等教育规章》(第18/2018号行政法规)和《高等教育学分制》(第19/2018号行政法规),进一步夯实了依法治教的基石。
(二)人才政策从封闭保守向自信开放转型
人才是干事创业的根本所在,是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对于劳动力市场容纳量不大且产业单一化程度严重的微型社会而言,任何通过引进方式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举措都将引发对岗位竞争加剧的担忧,甚至产生排斥心理,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就业不充分的历史时期。回归初期,澳门用人单位和社会团体对外劳的输入都持保守态度,陷入“本地人才培养不足,外部输入不够”的境地[16]。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对人才政策进行了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调适。
第一,明确提出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回归初期,对于人才的引进,第一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施政报告中仅仅提及“政府将致力于降低本地工人的失业率,积极推动职业培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输入外劳的政策”[17]。在外来人口增长方面也有诸多限制,明确提出不会考虑在可见的未来大量增加外来劳动力。此后,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彻底扭转澳门经济低迷的同时,也引发对专业人才话题的关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为使澳门的博彩业走向现代化、国际化,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决定开放博彩专营权,这不仅直接刺激了博彩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对博彩管理和专业人才提出了更多、更高的需求。2005年,第四届东亚运动会在澳门成功举行。经济的快速恢复以及传统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也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看到了人才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领作用。因此,自2002年开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每年的施政报告中均提及了人才引进的话题,社会应该重视发掘现有人才,给他们提供发挥才华的机会,使澳门逐步成为一个涌现人才、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的地区。2002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将适当引进外地专业人才,使其协助推动澳门的发展,并辅助本地人才的成长。[18]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实践,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明确提出“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并作为重要的施政方向加以持续推进。
第二,强化人才发展的顶层设计。为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2014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了人才发展委员会,主席由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兼任,成员主要来自社会文化司、教育暨青年发展局、劳务事务局、部分公立高校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等,主要承担三项职能:一是负责制定、规定及协调特区人才培养的长远发展策略,落实“精英培养计划”“专才激励计划”“应用人才促进计划”;二是建立鼓励人才留澳和回澳的机制;三是推动协调与人才培养相关的本地、区域及国际合作等各项工作。委员会下设规划评估、人才培养计划和鼓励人才回澳三个专业组,制定19项发展策略、45项措施或项目,由人才发展委员会和约15个相关负责机构或部门执行。至此,澳门人才队伍建设确立了引进、培养和回流三轨并行的策略,也形成了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专门负责人才队伍建设的管理体制。2018年,该委员会发布《中长期人才培养计划—五年行动方案》,该方案聚焦重点领域紧缺人才、产业多元人才、中葡双语和海洋经济人才等,旨在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该方案还明确了特区行政长官专门负责人才队伍建设的管理体制。[19]
第三,制定若干重要人才制度和计划。为进一步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增强引进效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制定了《人才引进法律制度》,2021年11月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2022年7月经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会讨论通过。该法律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定额、定向、定点的方式推进高端人才、优秀人才、高级专业人才三类专项计划,重点引进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科技、文化体育产业四大新产业的人才。高端人才计划不设限额,主要是指具备超凡才能或技术并拥有公认杰出成就的人;优秀人才计划设限额,指在某一专业或某行业中表现卓越的领军人物;高级专业人才也设限额,通过澳门公司雇佣或创业、评分等方式申请澳门身份。
针对当地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现状,人才发展委员会从2017年开始,推出“人才培养考证激励计划”,主要是提升当地居民个人职业技能,满足经济发展水平对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同时也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储备各类人才。
为鼓励澳门人才回流,建立了澳门人才回流资讯平台,并设立“澳大濠江学者计划”“教研及行政人员回澳短期工作奖励计划”,向不同专业、不同职位、不同类别的澳门人才提供短期及长期的配比计划,鼓励人才回流。前者主要面向在著名大专院校完成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澳门地区永久居民;后者则鼓励正在外地从事教研工作或高等院校行政工作且持有澳门永久居民身份证的人士,利用其学术休假或自身假期回澳短期工作,每月奖励2.5万澳门元,最长可资助12个月,其目的是增进他们对澳门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以备将来回澳门工作。此外,针对外来聘用人员,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组织编写了《人才需求清单》和《重点领域紧缺人才目录》等指导性文件。
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开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加大了人才流动与共享的力度。2021年,澳门与珠海签订了《关于推进澳珠人才协同发展的合作协议》,探索试行“一试双证”制度,创新两地技能人才认定工作,澳门劳工事务局还与珠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署《推动珠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框架协议书》,拟对电工、智能楼宇管理员、烹调师和保育师等工作开展培训认定工作。
三、启示
经过上述多重政策调整,澳门高校人才发展基本上实现了从自由发展到政策引领发展的模式转型。当然,在此过程中,澳门高校人才发展也暴露出一些内在的短板和不足:一是人才发展依托的平台载体有限,高等教育注册学生总数甚至不及内地一所大学的在校生数,自身的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也还有待增强;二是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如教学与科研的失衡,高层次人才储备量不够,在国际上有学术影响力或行业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数量更少;三是人才发展的溢出效应尚不明显等,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方面的支撑度和贡献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如此,由于澳门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区位优势,高校人才政策的调适还是为内地高校尤其是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了前期的探索和后续的启发。
(一)对内地高校人才政策的启示
第一,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及适度的福利待遇。数据显示,2021年澳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350,445澳门元。[20]充足的财政资金也为高校人才的收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内地高校而言,虽然经济发展程度区域间存在差异,但也要尽力加大高校经费投入,提升高校人才收入水平,同时改善高层次人才的福利待遇,从关注个人到覆盖家属甚至科研团队方面分步递进。
第二,要切实提升高校人才治理水平。一方面,要继续强化政府在高校人才引才、育人和用人方面的引导作用,协助高校在人才发展方面破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积极营造有利于高校人才发展的外部友好型环境;另一方面,要强化高校在人才发展方面的主体作用,尊重高校在引才、育才、用才、评才方面的第一责任人的地位,在人才评价、人才激励等方面真正为用人主体授权,还要优化高校内部人才机构设置,聚焦人才的主责,积极为人才减负,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约束和琐碎事务,让人才安心、专心教学科研和教书育人;同时,还要倡导社会的积极参与,共同丰富创新高校的引才方式、育才模式和用才形式,最终形成政府引导、高校主体、社会参与的高校人才治理架构。
第三,严格控制人才认定标准和程序。出于对本地就业人才的保护,澳门采取了“宁缺毋滥”的措施,加大力度控制对人才引进工作的责权分工和程序标准。在《人才引进法律制度》中,明确由人才引进评审委员会、人才发展委员会及治安警察局作为执行本法律的主管实体并制定相关职责。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有权核准各类人才引进计划,并对按照各类人才引进计划提出的居留许可申请作出决定,还有权制定各类人才引进计划、获批准的居留许可的特别规定及相关的税务优惠措施。澳门高校也基本上遵照上述程序来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对于内地高校来说,优秀人才相对短缺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用于人才队伍建设的经费也相对不宽裕。解决这对矛盾,各高校一方面要协同党委组织部门进一步规范并简化高层次人才认定的程序,另一方面,在人才供给量不断增加的新背景下,还要适度提高人才认定的标准,确保引进名副其实的好人才、真人才。
第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高校的人才,并不是只服务高校。他们也是服务社会、为社会作贡献的主力军。因此,在高校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仅仅依靠政府和高校单一且有限的专项经费投入难以为继,这需要倡导广大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捐赠资金,共同支持高校引进人才。澳门科技大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起来,固然与其重视国际化人才队伍的战略密不可分,但也离不开澳门企业的大力支撑,如为配合澳门科技大学人才引进计划,澳门知名企业永利度假村(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捐赠300万澳门元,设立“镜海学者计划”,专项用于人才引进,尤其是重点引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需求方面的人才。[21]
(二)对内地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启示
2014年之前澳门的人才引进观念还相对滞后,针对容量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对是否需要引进外专人才,社会各界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终于达成了一定范围的共识,在充分保护本地人就业质量的前提下,适度引进外专人才并促进澳门优秀人才的回流,以此来实现与本地劳动力共同发展的格局。在此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施政理念,不仅重塑了人才治理架构,理顺了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加大了政府投入,并推行了更重要的人才政策,虽然起步较晚,实施时间不长,但总体效果令人满意。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主动干预的措施外,还要得益于其在人才引进等方面具备的优势,如国际化的平台、中西文化的底蕴以及相对优厚的待遇等。从长远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加速推进,澳门高校办学实力的逐步提升,他们在人才引、培、用等方面的优势会更加明显。这为内地高等教育发达地区的高水平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借鉴。
第一,增强高校高层次人才和团队的引进建设力度。实践证明,人才引领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通过引入高端人才,建设一流学科,形成一个创新团队,带动一个产业发展,已经成为高校与政府部门的共识。例如,北京和上海的高层次人才密度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具有中国科学院以及上海科研机构的聚集优势,具有较好的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平台。因此,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高校根据自身定位,科学合理界定办学方向及发展战略,从学校自身的教学科研、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以及服务地方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总体规划,做好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同时要点面并重,注重加强科研团队的成建制引进。做好单个顶尖人才引进工作的同时,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着力打造高峰团队,使领军人才从一般性基础工作中解放出来,真正登上高峰占领学术高地,走到团队前列,引领学术前沿。
第二,提高人才获得感和幸福感。可优化人才住房保障政策,优化公租房供给配置,完善引进人才租房补贴优惠制度;加强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保障,将各类人才子女入学政策纳入当地人才工作体系,由人才部门认定标准和范围,按照既有工作机制进行梯度化保障;支持相关科技单位与有关区和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由有关区按照同等条件人才标准和程序予以保障和适当照顾;探索实行分类施策的办法,建立校地协同解决机制;妥善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医疗保障工作。例如,北京和上海拥有全国较为丰富的医疗资源,在不拼重金、拼服务的理念指导下,要消解全国其他地方依然通过重金来引才所带来的压力,要继续完善高层次人才疗休养制度,提供就医便利服务,并逐步扩大覆盖面,保障高层次人才身心健康。
注释:
①人类发展指数按照得分高低划分为四种等级:极高、高、中、低,得分0.8以上的为极高等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 习近平: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EB/OL].(2021-12-15)[2024-01-26].https://www.gov.cn/xinwen/2021-12/15/content_5660938.htm.
[2]张红峰.回归十五年澳门高等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广东社会科学,2014(6):101-109.
[3]澳门统计暨普查.教育调查[EB/OL].(2022-10-12)[2023-02-04].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bb14a692-e659-4323-ab42-362a16b98b43/C _EDU_PUB_2000_Y.aspx.
[4]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澳门统计年鉴2002[EB/OL].(2003-07-16)[2024-02-04].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c0ce42c5-3c94-40e3-8de6-505594b8e154/C_AE_PUB_2002_ Y.aspx.
[5]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澳门统计年鉴2011[EB/OL].(2011-08-20)[2024-02-04].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c0ce42c5-3c94-40e3-8de6-505594b8e154/C_AE_PUB_2011_ Y.aspx
[6]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澳门统计年鉴2022[EB/OL].(2023-11-15)[2024-02-04].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f8aafaff-565b-4b56-a02a-faddae2b5bf5/C_AE_ PUB_2022_Y.aspx.
[7]祝晓芳,马早明.回归20年澳门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发展:成就、问题与展望[J].江苏高教,2019(11):11-17.
[8]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澳门高等教育资料2010/2011年度教职员及学生人数[R].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2011:6.
[9][10][11][12]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局.高教统计数据汇编2019[G].澳门:高等教育局,2019:7,8,9.
[13][17][18]何厚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二零零零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EB/OL].(2000-03-29)[2023-04-20].https://www.gov.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17/11/cn2000_policy.pdf.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教育局.澳门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2021-2030)[EB/OL].(2020-12-28)[2024-02-04].https://www.dses.gov.mo/HEMLD.
[15]韦蕙蕙,张光南.澳门回归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2(2):18-23.
[16]刘雪菲.注重引进、培养、回流三轨并行,构建澳门人才“储备池”——如何破解澳门人才缺乏之困?[J].澳门月刊,2021(9):34-35.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中长期人才培养行动方案文本网上公布[EB/OL].(2018-01-04)[2023-05-06]. https://www.gov.mo/zh-hans/news/191187/.
[20]新华网.澳门2021年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8%[EB/OL].(2022-03-04)[2024-02-04].http://www.xinhuanet.com/2022-03/04/c_1128438882.htm.
[21]澳门科技大学.澳科大获永利支持“镜海学者”高端人才引进[EB/OL].(2021-12-07)[2023-07-18].https://www.must.edu.mo/cn/news/42017-article12072148-c.
Adjust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Talent Policy Since
It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ZHOU Jianglin1,2
(1.The Institute for Higher Education,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China;
2.Lab for Educational Big Data and Policymaking, Shanghai Academy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China)
Abstract: Universi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gathering and cultivating of high-level talents. Since its return,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in an orderly manner, with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total number of university tal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agglomeration effects.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Macau SAR government’s timely adjustment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talent policies, which positively guide and optimize the talent development at universities. Thus, Macau’s higher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disorderly development to goal-driven development with a shift in talent policy from being closed and conservative to being confident and open. These experiences offer insights for mainland universities in providing competitive salary and welfare benefit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abilities of talent governance at universities, implementing rigorous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for talent identifi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 public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talent hubs can be a useful strategy to attract high-level talents at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al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and happiness.
Keywords: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alents in universities; Talent policy
编辑 吕伊雯 校对 王亭亭
原标题:回归以来澳门高校人才政策的调适与启示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4-04-08 12:00:00
时间:2024-04-08 1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