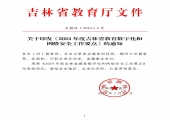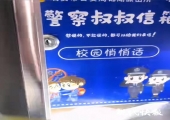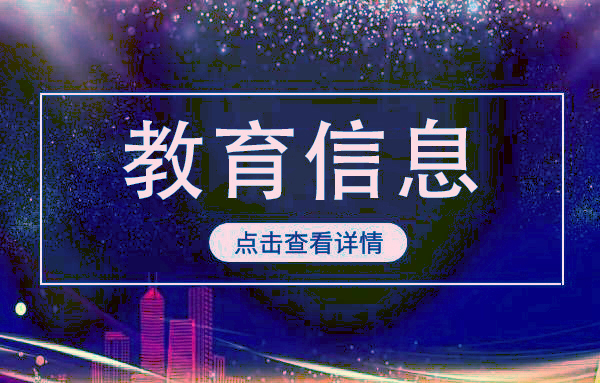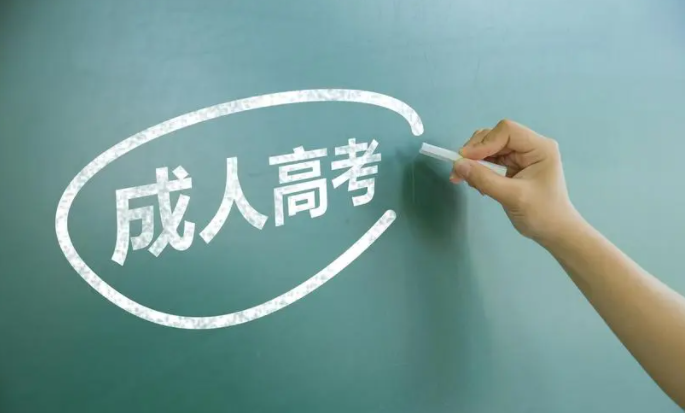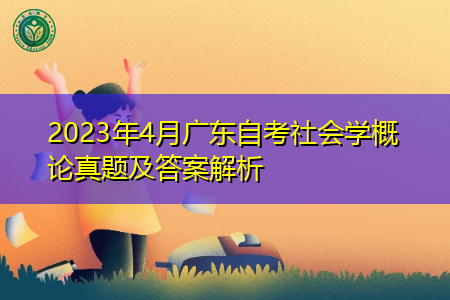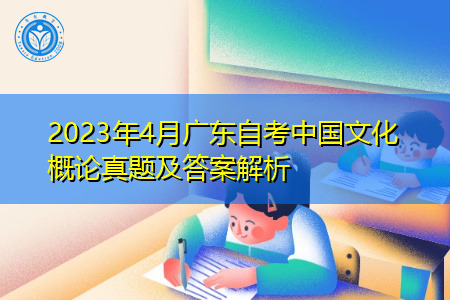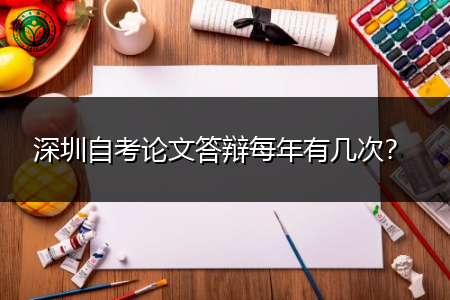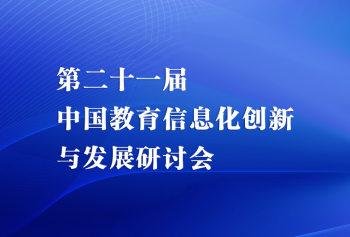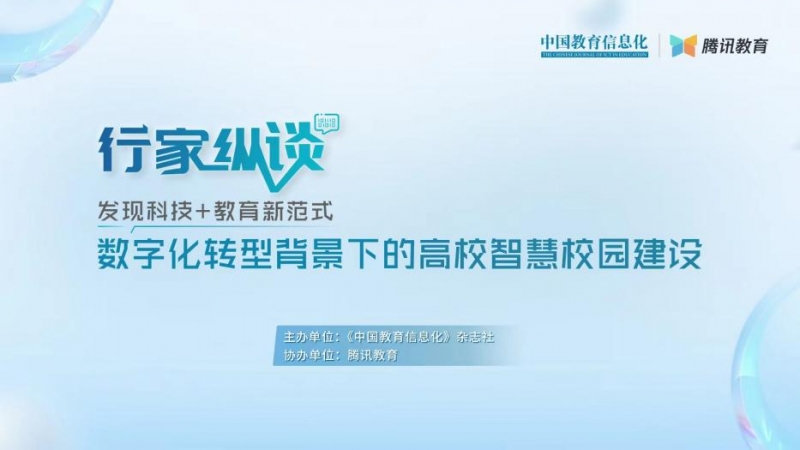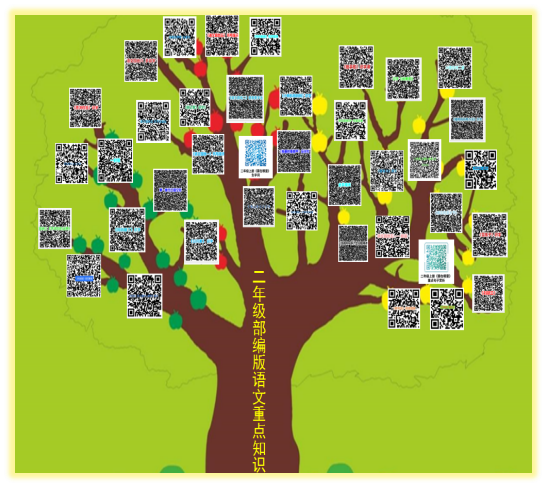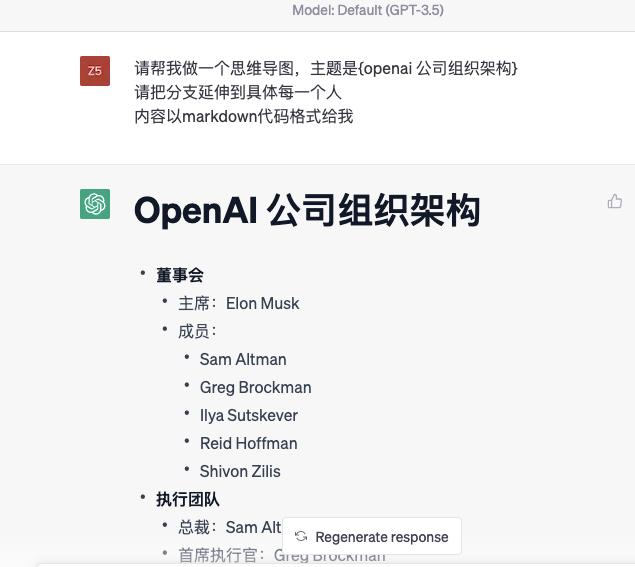摘 要:有组织科研机构是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前沿科技发展的重要形式。美国加州大学系统通过组建多种形式跨学科、跨校区、组织化的有组织科研机构,制定系统的组织管理制度,鼓励有组织科研机构联动多元主体推进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迅速发展。这种科研组织模式对我国深入推动有组织科研有以下三方面借鉴:厘清有组织科研机构的角色定位,强化主体协同共建;优化有组织科研机构治理机制,提升组织效能;完善对有组织科研机构的过程性评价制度,实现以评促建。
关键词: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科研机构;美国加州大学系统;科研组织形式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陆程程,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赵宏媚,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姚建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讲师(上海 200240);赵文华(通讯作者),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高校科技创新团队管理与合作有效性研究”(编号:22&ZD308);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2023年度国外教育研究委托课题“医学教育国际比较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编号:EMIC-YJC-20230006);上海市软科学研究项目“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路径与对策研究”(编号:23692100800)
有组织科研是高校深化科技创新,建制化、体系化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前沿科技发展的重要形式。二战后,有组织科研在美国获得世界科技中心地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推动美国产生大量卓越的科技成果。在诸多有组织科研参与形式中,建立有组织科研机构(Organized Research Unit,ORU)是美国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重要形式。
加州大学系统是美国公认教育质量最高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之一,由10所世界级综合大学构成: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圣巴巴拉分校、戴维斯分校、圣地亚哥分校、欧文分校、河滨分校、圣克鲁兹分校、旧金山分校和莫塞德分校。各高校在202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球排名中均位于前100名,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更是位列前20位名。[1]各校区高度自治,在招生、财政、科研等方面拥有独立的管理权限,仅在部分学术资源上共享。各分校优势专业各异,依托ORU孵化出众多企业,涉及生物技术、计算机、半导体、电信和农业等领域,已成为加州经济发展的加速器。目前,加州大学拥有全美18个国家实验室中的3个,即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2]上述实验室均隶属于美国能源部,承担美国国防安全关键任务和重要课题,已获多项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鉴于美国加州大学系统在有组织科研实践中的代表性,本研究以其为例,梳理其有组织研究机构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高校科技发展提供模式借鉴。
一、组建跨学科的有组织科研机构
建立跨学科的ORU是加州大学各分校推进科研创新的重要形式,主要包括研究所、实验室和研究站等。ORU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关键载体,通过聚集不同院系、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专职研究者、博士后与科学家就某一课题开展研究,能够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形成科研攻关合力。目前,洛杉矶分校有18个ORU,科研领域涉及非洲政策、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伯克利分校建设ORU的热情更为高涨,其围绕国际事务、信息技术、环境等领域建设有100多个ORU。
在类别上,加州大学系统现有ORU可分为两类[3]。第一类是基于单校区有组织科研机构(Single-campus Organized Research Unit),旨在为所在校区服务,由分校校长统筹ORU的管理、预算、场地等。例如,圣巴巴拉分校成立于2005年的弗农和玛丽—钱德尔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恢复中心(CCBER),由系统学与生态学博物馆和“生态恢复计划”联合建设,旨在保护和恢复校园附近的湿地栖息地。在穆勒(Muller)博士创立维管植物馆藏资源之后,多位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相继加入,在生态学、行为学、植物结构和现代系统学发展方面取得前沿的研究成果。[4]第二类是在加州大学系统的层面上建立的跨学科组织——多校区有组织科研机构(Multicampus Organized Research Unit)。该类ORU经由大学学术评议会评审与批准正式建立,隶属于整个加州大学系统,最显著特征在于拥有异质性研究设备与科研人员,打通了学科、学院以及分校的边界,主要分为在两个及以上校区研究所、实验室和研究站等拥有设备和人员的ORU,以及在单校区拥有设备,但人员来自其他分校的ORU。由于单个分校并不可能在所有学科上拥有绝对优势,且不具备绝对充足的资源储备,而多校区ORU的筹建能以最小协作成本,最大化利用加州各分校的资源,优势互补,实现整体竞争力最大化,因而多校区ORU成为加州大学系统推进国家重要项目的首选。例如,在美国能源部的资助下,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与国家实验室密切合作(劳伦斯利弗莫尔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等),优化升级半导体芯片生产技术。[5]多校区ORU也积极将基础科学和工程研究与符合国家利益的劳动力发展计划相结合,联动科研单位内各背景学者共同开发天体物理等行星科学相关课程,激励博士后学者、研究生以及本科生、高中生追求直接或间接支持美国国家实验室使命和劳动力发展需求的职业。
二、制定系统的有组织科研机构管理制度
(一)部门主任负责制和顾问委员会制耦合
学术共同体和行政体系良性共存于ORU管理体制,有效推动了科研探索。为鼓励跨学科交流合作,加州大学形成专门针对单校区ORU、多校区ORU组建申请、项目申报、资金使用等的组织管理制度。同时,鉴于不同学科的认识论、研究范式,以及不同学者的主张、学科理念存在差异,加州大学系统建立了一个上位机构以调和冲突,推进跨学科研究。[6]在行政程序方面,加州大学系统建立通畅与开放的各层级负责制度与相应的报告制度,有效降低了组织运转成本,更精准对接下一级ORU。整体而言,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加州大学系统ORU现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实现了跨学科研究组织权力的动态平衡,保持了组织间合理张力与跨学科研究动力。[7]
ORU实行部门主任负责制,将行政权力分配到跨学科研究组织的负责人手中,直接对接所属分校或总校。经由分校校长与学术顾问委员会一致提名,在后者推选基础上,分校校长对单校区ORU 主任进行任命。[8]多校区ORU主任是总校分管科研的副教务长在征求相应分校校长意见,并通过招聘委员会审议的基础上予以任命。招聘委员会成员由分管科研的总校副教务长在总校学术委员会主席以及相关分校校长中征集。
ORU推行顾问委员会制。由于学术顾问委员会的指导与咨询对于解决学术权力层面的冲突具有积极意义,顾问委员会制成为各ORU的常设制度。单校区ORU主任由学术顾问委员会推选。同时,该委员会任命由一名非本ORU主任的教师任委员会主席,其余成员主要是教师。委员会定期举办研讨会,讨论设立ORU的目标,严格评价ORU的效率,并向单校区ORU主任提供建议。委员会主席及成员需要接受每五年一次的评估,其具体的责任与功能、成员、报告制度由分校的分管校长决定。多校区ORU顾问委员会在尊重分校校长的基础上由总校校长任命。多校区ORU可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委员会提供辅助咨询,如校外顾问委员会由来自政府机构、私营部门与公共非营利部门的成员组成,可以对多校区ORU的募资方式和途径提供指导。校外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则由总校校长任命。
此外,为实现对单校区ORU、多校区ORU的高效科研管理,加州大学系统基于项目管理目标,将依托原有组织资源但独立于原有组织结构外建立的矩阵式结构置于大学科层管理结构之中,形成一个制度化且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9]通过相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多校区ORU加以约束,联动不同单位的人员、资金、设备推进研究,避免因归属不同等原因导致的合作难以推进,有效加强了组织凝聚力。例如,伯克利大学为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的巴卡尔地球数字材料研究所(BIDMaP)便采用了上述矩阵式结构。[10]该研究所由湾区基金会(Bay Area Foundation)、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办公室等提供资金,由统计系、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系、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小组伯克利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提供技术支持,由计算、数据科学和社会学院(Division of Computing, Data Science, and Society)的副教务长和伯克利信息学院的院长提供顾问指导。
在职能分配上,单校区ORU主要向分校校长负责,多校区ORU主要向总校校长负责。总校校长在整体性政策与项目中,具有协调各校区资源的最终责任与权利;多校区ORU所在分校校长必须监管其与其他分校之间的行政关系。这种科层管理制也典型地体现在单校区ORU的创建与年度汇报等管理之中。以年度报告制度为例,在每学年结束之际,每个单校区ORU需要向主任提供年度总结,报告的生成和有效性需要经过顾问委员会主席审议,内容包括研究贡献、研究人员数量、出版物清单、经费支持情况等。同时,为确保分管科研的总校副教务长准确掌握加州大学系统中单校区ORU的信息,分校校长必须呈报年度报告,阐明该学年单校区ORU的创建与撤销,以及单校区ORU的中长期评议总结。各多校区ORU也须给分管科研的总校副教务长提交年度报告,公示其在不同分校校区内的工作进展,并汇报来自不同校区科研人员的参与情况。
(二)建立阶段性定期评价制度
定期评价现有ORU有助于保持其组织活力,为分析是否持续推进计划和目标、开展同行评审评估创造机会;同时,向行政部门提供存在合理性的证明,确保正在进行的研究质量得到保障、研究经费和人员安排配置得当。由于ORU在设立之初就是目标导向,阶段性评估与其追求效率的特征保持一致,关注研究使命与目标实现程度,确保研究的高质量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此过程中,效率低下的ORU或者重复设置的ORU在被评估后可能被取消或者合并。
加州大学对ORU开展的定期评价依据评价周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期五年(或五年以内)的定期评价,以确保研究的高质量开展、学校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和保持学校的特色与优势。其评价内容主要为ORU的初创目的、研究成果、发展规划和与研究方向的可持续性,旨在审查该组织在此期间是否完成先前的预定目标、是否根据目标调整计划、是否能针对新的目标制定新的步骤与措施。另一类是对ORU每隔15年的生命周期评价,主要关注学术、科研价值以及各分校或学校的优势,评议该机构是否应继续存在与发展。在展开评议前,ORU需要形成一个关于自身地位、支持经费、当前大学需求与资源空间方面的自我评价报告,为其继续存在陈述具有说服性的基本理由,并总结过去15年的成就、贡献以及撤销后的可能结果。在接受15年周期评议委员会的评议以及学术评议会和行政管理官员的评审后,单校区ORU与多校区ORU分别由分校校长和总校校长做出撤销、延长或者其他变更的决定。[11]
在对ORU的定期评价中,评价主体具有不同学科背景,评价内容涵盖单一学科的同行评议,并注意适应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特性,彰显对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多校区ORU的评价制度与单校区ORU保持一致,主要目的与评价内容也基本相同,仅在评价层次上存在差异。多校区ORU在评价委员会的生成与评价管理层次上要高于单校区。单校区ORU主要是置于分校一级的管理层次上,由各分校校长组织专门评议委员会进行评议;多校区ORU是置于加州大学一级的管理层次上,由分管科研的总校副教务长负责进行。
三、鼓励多元主体联动推进项目实施
(一)积极吸纳校内多元背景个体
ORU的持续创新力来源于其组成人员的多元化。ORU鼓励相关背景的研究团队或个人参与相关项目。其为附属机构及校园人员提供参与渠道,鼓励任何与ORU使命和活动相匹配的教师、研究人员或学生参与,进行科研任务攻关或担任科研助理;广泛吸纳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事斯特伍德校区和附属站点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加入研究项目。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查尔斯·R.德鲁医学与科学大学艾滋病研究中心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下,广泛吸纳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韦斯特伍德校区和附属站点的研究人员加入研究项目(主要涉及港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的伦德奎斯特研究所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大洛杉矶医疗保健系统);同时,积极为研究人员、年轻学者提供进入社区参与研究的机会以增加艾滋病毒研究人员的多样性。[12]
(二)广泛拓展校外研究合作网络
随着全球科研竞争日趋激烈,个体研究者“单打独斗”式的科研模式并不利于难题攻关。不同层次研究者、科研机构的加入增加了研究团队的异质性,可以最大程度上激发不同主体的优势。加州大学积极与企业、国家实验室建立联系,在开展纯基础研究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围绕关键政策领域的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开展关键技术领域的科研创新。其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生产新知识、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推动生命科学、工程科学等学科的投入,以提高美国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空间技术等未来领域的全球科研竞争力。[13]伯克利大学的法律研究所在多个单位(如加利福尼亚海洋赠款计划、加州大学海洋理事会、环太平洋研究计划、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和福特基金会等)的资助下,与政府研究所、罗宾斯宗教协会、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华盛顿大学、仁荷大学(韩国)等主体合作,深耕环境法与政策、宪法与历史等领域,享有极高的全球声誉。[14]
四、结语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全球科研竞争日趋激烈,通过有组织科研增强自主创新力不仅是增强我国在全球科学体系中的话语权的关键途径,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2022年8月29日,教育部印发《关于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15],明确提出“高校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技创新实现建制化、体系化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重要形式”,我国需厘清高校在有组织科研中的责任与地位,鼓励高校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然而,我国高校虽建成诸多研究所、研究中心,但整体呈现数量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的局面,在研究成果上也存在部分偏离我国发展需求等情况。因此,需要从组织建构本身重新思考高校参与有组织科研的深层逻辑。本文梳理美国加州大学系统有ORU的类型、申报与监管制度、评估与奖惩政策等,探究美国高校如何在既有的管理体制基础上,实现对ORU的高效管理,释放科研人员及科研团队创新活力,并提出以下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提供借鉴。
(一)厘清有组织科研机构角色定位,深化多主体协同共建
协同攻关是有组织科研的主要特征。推进高校有组织科研需要明确高校科研机构、研究所、研究中心等主体地位,同时保障其他多元主体的实质性参与、打破协同壁垒、加强多主体协同、实现知识与资源共享,形成科研合力。
一是建立专门、稳定、独立的跨学科研究管理部门。当前,我国的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基本由院系统筹,科研单位的主体性较弱。在人员构成上,大多由本院系负责授课的专职教师兼职。虽然不乏来自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但多为挂名,基本不参与项目的实质推进。基于此,可以在学校或更高层面设立专门的管理办公室,鼓励研究所、研究中心等积极引进其他相关方向的专职研究员,促进研究人员构成的多样性,确保实质性参与;定期邀请各院系学者参与工作研讨会,为推进跨学科知识交叉融合提供平台。
二是明晰角色定位,拓展大学伙伴关系,营造创新生态。长期以来,我国科研体制呈现由政府主导,通过行政力量凝聚全国之力实现科研攻关的运行特征。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部分关键科技领域的重要突破,但也存在其他各创新主体功能不够明晰、科研单位组织活力缺乏、科研成本较高且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基于美国在二战后大力发展ORU的经验,我国可注重吸纳其他多元主体参与科研合作,协同推进科技突破,增强国家竞争力。首先,我国可进一步明确大学作为基础科学研究中心和重大科技创新策源地的主体定位,鼓励其大力建设专业化科研单位,有组织深入推进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其次,政府在ORU的审核及项目申报过程中,可进一步发挥统筹协调作用,科学评估单位是否围绕相关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是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是否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等。最后,我国应积极发展大学与其他慈善机构、企业的伙伴关系,完善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慈善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举国科研体制,以充分整合各类可用资源,增强科研可持续性,营造利于创新的良性生态。
(二)优化有组织科研机构治理机制,提升组织效能
随着科研任务加重及异质性科研人员加入,ORU的规模会不断增大,一方面会推动研究开展的规范化,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增加行政负担,激化组织内部矛盾。由于国家科研资源有限,各科研团队会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准备申报材料,提高项目申报成功率,无形中降低组织活力和科研效率。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可在ORU既有的人事构成上,加大对组建科研助理队伍的重视。通过设立职业发展通道,培养专业、稳定的科研服务队伍负责项目申报、研讨会安排等工作,真正对科研项目起到高质量支撑作用。[16]同时,建设学术顾问委员会,将科研人员纳入机构决策过程,调整组织既有权力与利益格局,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相结合,增强科研人员的组织认同感,保证项目合理性被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充分讨论,在跨学科研究组织权力冲突间求得平衡,保持组织之间的张力与跨学科研究的动力。[17]
(三)完善对有组织科研机构的过程性评价制度,实现以评促建
为确保单校区ORU和多校区ORU的研究效率,我国需要建立中长期定期评价以按时监测研究单位是否高质量推进项目、学校资源是否得到合理配置;同时,引入生命周期评价,定期裁撤缺乏研究前景的研究单位,最大程度上保证研究单位的活力。目前,我国虽然不乏评价制度,但大多聚焦在前期审核和终期评估,在中期监测和退出机制的关注上相对不足。因此,我国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一是增加对研究中心及相关项目的中期评价。ORU在成长发展过程和项目推进过程中的质量与效率直接影响项目成效。美国在详细审核各ORU的组建申请、项目申报后,要求ORU提供年度报告,总结其科研贡献及组织效能,论证其是否达到目标及自身存在合理性,一定程度上通过给予科研单位危机感提升其组织效能。二是构建科研团队评价体系。当前我国的科研评价侧重于以高校为对象的机构评价,以及以科研人员为对象的个体评价,中观层面上的科研团队评价相对不足,难以充分释放团队创新活力。同时,在科研成果归属上,我国倾向于将成果归为主要贡献人及其所属单位,导致部分参与成员缺乏获得感与认同感,一定程度上阻碍跨学科、跨单位深入合作。针对上述问题,我国可构建一个高校、科研团队和科技创新人员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科学评价科研团队、科研人员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参与度及贡献,最大程度提高团队效能及个人创新意愿;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建立整合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的激励机制与弹性的奖励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同时,辅以流动机制和退出机制,为组织成员的流动和发展提供支持,避免组织僵化。
参考文献:
[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arns top spots in 2023-24 U.S. news best colleges rankings[EB/OL].(2023-09-18)[2024-01-17]. https://www.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news/university-california-earns-top-spots-2023-24-us-news-best-colleges-rankings.
[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About u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B/OL]. [2024-01-17].https://www.universityofcalifornia.edu/for-california/research.
[3][1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esearch.ORU policy & procedure guide[EB/OL].[2024-01-17].https://vcresearch.berkeley.edu/how/vcr-units/oru-policy-procedure-guide.
[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ara.A brief history of the UCSB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EB/OL]. [2024-01-17].https://ccber.ucsb.edu/collections-biodiversity/natural-history-biodiversity-collections-overview.
[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UC San Diego’s center of excellence receives $12.5 million from DOE[EB/OL].(2023-06-22)[2024-01-17].https://www.hpcwire.com/off-the-wire/uc-san-diegos-center-of-excellence-receives-12-5m-from-doe/#:~:text=UC%20San%20Diego%E2%80%99s%20Center%20of%20Excellence%20Receives%20%2412.5M,excellence%20at%20the%20University%20of%20California%20San%20Diego.
[6]罗杰·盖格,高筱卉.论美国大学中有组织的研究单位[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3(5):171-180.
[7]潘教峰,鲁晓,王光辉.科学研究模式变迁:有组织的基础研究[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1,36(12):1395-1403.
[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ARARAS.Organized research unit administration[EB/OL].[2024-01-17].https://www.research.ucsb.edu/organized-research-unit-oru-administration.
[9]周朝成.加州大学跨学科研究的组织结构与制度研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9(3):101-106.
[10]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esearch.New institute brings together chemistry and machine learning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EB/OL].(2022-09-21)[2024-01-17].https://vcresearch.berkeley.edu/news/new-institute-brings-together-chemistry-and-machine-learning-tackle-climate-change.
[12]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 Charles R. Drew University receive $11M grant to address inequities in HIV care, prevention[EB/OL].(2023-03-23)[2024-01-17].https://newsroom.ucla.edu/releases/center-for-aids-research-nih-grant.
[13]谷贤林,李乐平.美国《无尽的前沿法》议案解析[J].世界教育信息, 2022, 35(4): 19-26.
[1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egal research[EB/OL].[2024-01-17].https://vcresearch.berkeley.edu/research-unit/institute-legal-research.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EB/OL].(2023-08-09)[2024-01-17].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8/t20220829_656091.html.
[16]林小英,林心颖.高校个体竞争与学术合作困境:“首席研究员制”下的科研助理聘用考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41(1):60-74.
[17]谢宝剑,余贞备.“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研讨会综述[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126.
The Practical Pathway and Insights of Establishing Organized Research Unit
at Public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aking 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as an Example
LU Chengcheng1 ZHAO Hongmei1 YAO Jianjian2 ZHAO Wenhua1✉
(1.School of Education,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China;
2.Division of Research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Organized Research Unit(ORU)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form for universities to serve the needs of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frontie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encouraging ORU to collaborate with diverse entities, establishing various forms of interdisciplinary, cross-campus, and organized research units, and implementing a systematic management system for ORU. This organizational model provides three aspects of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China to further promote organized researches: clarifying the role and positioning of ORU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among entities;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ORU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mproving the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for ORU to promote construction through evaluation.
Keywords: Organized research;ORU;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form
编辑 王亭亭 校对 朱婷婷
原标题:美国公立高校建设有组织科研机构的实践路径和启示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4-04-08 12:00:00
时间:2024-04-08 1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