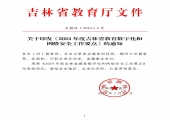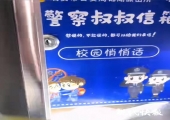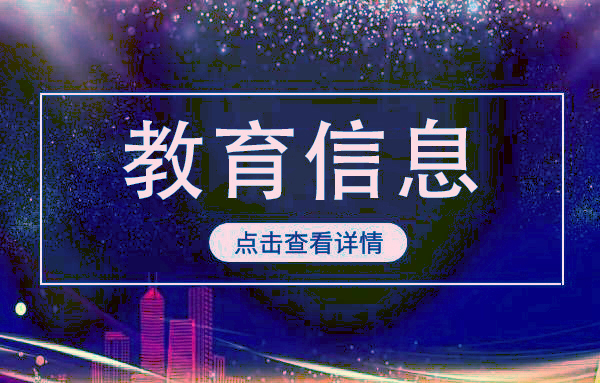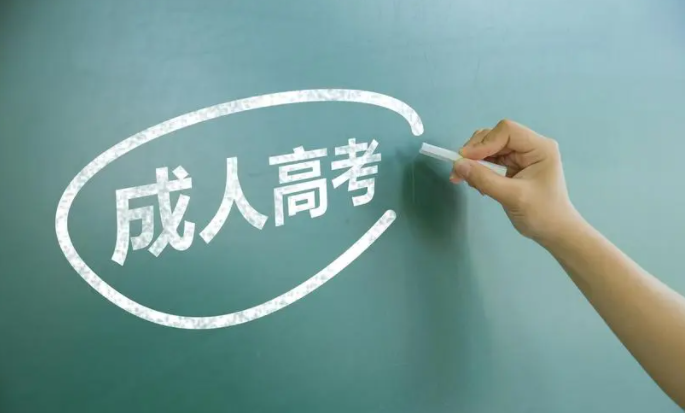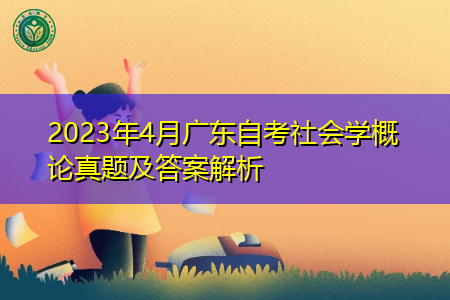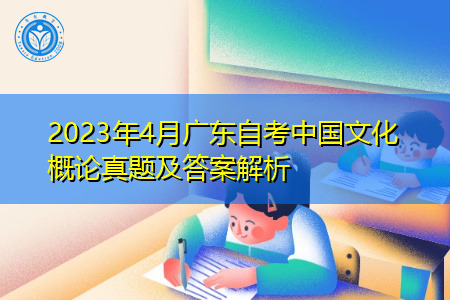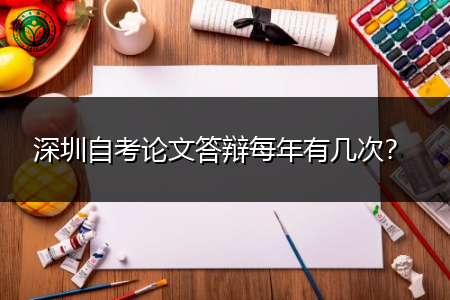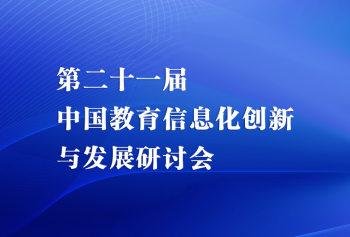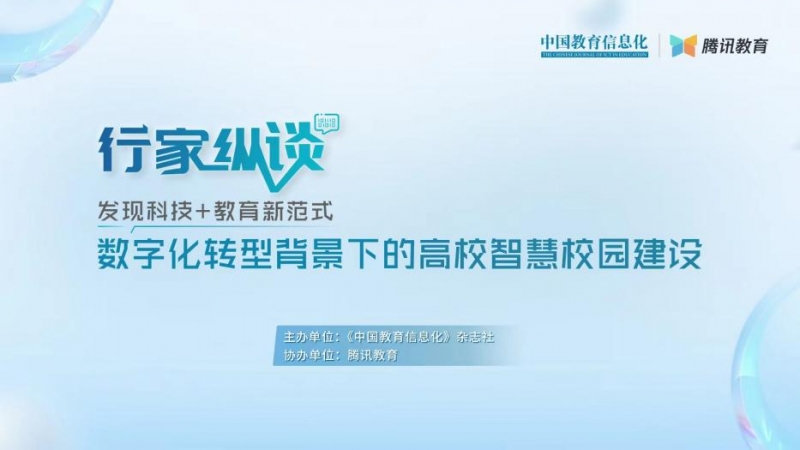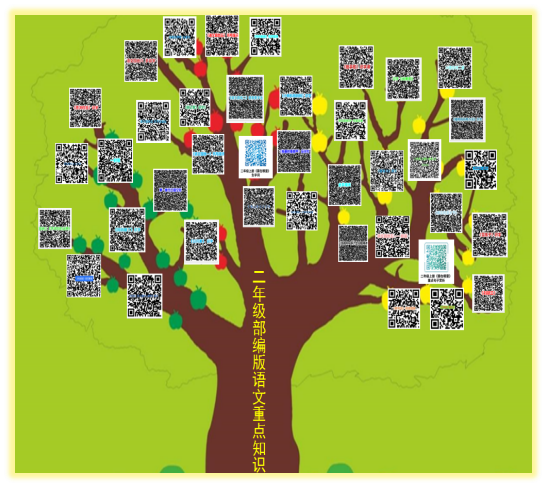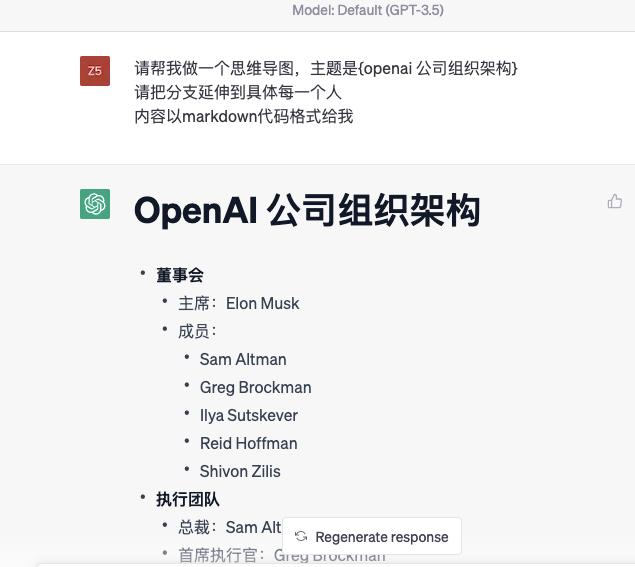摘 要:“一带一路”为扩大教育开放,增强国际人才培养与合作创造了条件、搭建了桥梁。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开放方面存在着深厚的合作基础和潜力。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民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开展了多样的合作;也在产教融合、国际组织人才和新型数字化人才培养等领域实现了新拓展。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人文交流领域可实现层次更高、力度更深、影响更强的制度型开放。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东盟;鲁班工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新型数字化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513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周满生,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816),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原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北京 100816)
习近平主席在《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1]。
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为扩大教育开放,增强国际人才培养与合作创造了条件、搭建了桥梁。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同属亚洲,文化、风俗相近,文化和教育交流由来已久。东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发源地。自2003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教育等领域延拓,中国与东盟不仅是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在教育合作领域,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相对较少,存在进一步合作的扎实基础。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既包括全民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传统合作领域,也包括新的教育领域,如产教融合发展、国际组织人才和新型数字化人才培养等。
一、中国—东盟合作覆盖各级各类教育
(一)全民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十国在全民教育领域有长期的教育合作。1990年3月,在泰国宗滴恩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会议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提出全民教育,倡导满足儿童、青年及成人基本学习需要,强调全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动员和组织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全民教育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两个文件对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有重大影响。该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总目标极具时代性、全局性、前瞻性。中国政府也如期实现了这个总目标。中国实施全民教育进程明显快于全球,中国对提高全球人类发展水平作出了贡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1990—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54.2%,提前3年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极贫人口减半的目标,在这些减少的贫困人口中,中国贡献了63%。[2]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为89.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5.5%、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91.6%。[3]中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总体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有学上”的需要。中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80%左右学生的学业表现达到中等以上水平;部分省份连续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总体成绩名列前茅。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教育人口大国,学龄儿童数量庞大,是发展中大国办大教育的典型。中国在基础教育中的成就,特别是为上亿的学龄人口提供免费、公平而有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对国际减贫事业的贡献。东盟国家学龄儿童数量庞大,除新加坡外,基础教育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中国普及义务教育的经验可部分为东盟国家借鉴。同时,基础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如流动人口子女和留守儿童的受教育问题也可以相互学习借鉴。
双方在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领域的合作也大有可为。中国—东盟中心在促进多双边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上发挥了桥梁作用,以载人航天相关的合作为例,2022年11月,神舟十四号三名航天员在太空中与中国和东盟国家青少年,在北京王府学校进行了一场“天宫对话”问答互动活动。来自中国以及文莱、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的青少年向航天员们踊跃提问,并一一获得细心解答。该活动的主会场设在北京,另外分别在文莱、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地设立分会场。中国和东盟国家青少年、媒体代表等近千人参与活动。在北京主会场与海外分会场连线中,东盟国家青少年代表就航天员在太空中最大的挑战、是否可以使用手机并上网、如何喝水进食、男女航天员的差异、成为航天员最重要的素质等问题纷纷提问,三位航天员对此细心解答,也寄语青少年们的航天梦早日成真。[4]
(二)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有长期的合作,相互派遣了大量留学生。QS公司于2023年11月发布了2024年亚洲大学排名。[5]排名包含来自亚洲18个地区的856所高等院校,是QS对亚洲地区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比较评估。本次排名基于11项评估大学表现的关键指标,以展现其学术地位、毕业生就业能力、研究质量和生产力、校园国际化程度,以及每所院校国际合作的多样性。北京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排在榜单的前四位(南洋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列第四)。马来亚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等也名列榜单前列。国际学生数量在国际上已成为评价一所大学国际化水平、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位次越高,吸引的国际学生质量越好越多,国际学生质量越好越多,就越能提高大学的知名度。这些亚洲大学无论在与我国高校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还是在接受我国留学生方面都有着杰出的表现。
(三)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生源和就业不佳,劳动力市场“招工难”和“就业难”问题同时存在,技能劳动者比例偏低且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匮乏,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从2019年开始,中国发布了一系列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对职业教育地位、办学主体、培养目的、财政支持、未来发展方向等多方面做出进一步明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道路、能源、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不断扩大。新加坡职业教育起步较早,逐步解决了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学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社会脱节的问题,如积极与跨国公司签订人才培养合同,联合制定培养方案,很快培养出一批实践能力强的高技能人才,其经验或可为我国解决职业教育结构性矛盾所借鉴。
二、中国—东盟教育领域合作的新拓展
(一)产教融合发展
中国可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构建、师资和员工培养、实训条件建设、教学组织等方面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构建办学新机制,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建设东盟国家开放交流的新平台,制定紧密、实质的联合培养机制,使培养目标与用人标准相衔接。通过多方互动、联结与共享,真正达到产教融合,最终实现多方共赢与发展。例如,鲁班工坊是一种创新型国际职业教育服务项目,是天津市率先主导推动实施的职业教育国际知名品牌。以鲁班的“大国工匠”形象为依托,在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相继设立鲁班工坊。鲁班工坊通过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方式,将优秀的职业技术和职业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搭建起天津职业教育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又如,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中国在印度尼西亚投资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并在柳州市建立了中印汽车学院。该公司从印度尼西亚选拔并资助了260名学生到中印汽车学院接受汽车制造相关培训,从而为印度尼西亚的生产基地及相关产业园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
中国在培养国际组织胜任力人才方面与培养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具备国际组织胜任力的人才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中国亟需更多掌握议程设置能力、规则制定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的人才,掌握全球话语,面向未来,以新的方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而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等国拥有大量的国际问题专家、国际组织兼职人员,他们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工作,有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可以完善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与管理,将有助于发现、培养并选拔更多人才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新型数字化人才培养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之一,东盟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内数字经济融合。2021年,东盟发布《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旨在引领东盟2021—2025年的数字合作,将东盟建设成一个由安全和变革性的数字服务、技术和生态系统驱动的领先数字社区和经济体。[6]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新增长点。根据相关研究报告,预计到2025年,中国和东盟数字经济总量有望达到9.58万亿美元。[7]随着数字经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技能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对数字人才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数字经济将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教育新增长点。数字人才培养正从学科导向变为产业需求导向,人才培养的目标从服务数字经济转型转变为支撑引领数字经济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可以政府间合作为基础,以校企合作为基本路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5G等数字人才培养为重点,有机整合政策、人才、技术、市场等多种要素资源,打造中国—东盟新型数字人才培养发展体系。
三、结语
人文交流领域合作要在多双边相互尊重和信任平等的基础上才能持久开展,多双边应是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与和睦相处的好邻居。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顶风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舆论盛行时期,特别要尊重历史,避免无谓的价值观冲突。倡导层次更高、力度更深、影响更强的制度型开放;注重与高标准国际规则、管理标准对接。当前世界越来越多极化,国际交往中更多用的理念是去风险(de-risk),而不是脱钩(break off relations)。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化解政治与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可以增强互信,团结更多的民间乃至政府间力量。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人文交流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尤其如此。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2023-10-18) [2024-02-05].http://news.china.com.cn.
[2]吴国宝,等.中国减贫与发展(1978-201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3-14.
[3]国家统计局.2022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EB/OL].(2023-12-31)[2024-02-05].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7.html.
[4]搜狐科教观察.“天宫对话-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与东盟青少年问答”活动在北京王府学校举行[EB/OL].(2022-11-02)[2024-02-05].https://www.sohu.com/a/601974010_ 120619005.
[5]QS.Rankings released!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Asia 2024[EB/OL].(2023-11-08)[2024-02-05].https://www.qs.com/rankings-released-qs-world-university-rankings-asia-2024/.
[6]董宏伟,王琪.《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25》与基础设施建设[EB/OL].(2021-05-19)[2024-02-05].https://www.secrss.com/articles/31303.
[7]中国报道.中国—东盟数字人才培养交流合作前景看好[EB/OL]. (2022-04-14)[2024-02-05].http://www.chinareports.org.cn/djbd/2022/0418/27529.html.
ASEAN Countr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ners in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Opennes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ZHOU Mansheng1,2
(1.Former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Beijing 100816, China;
2.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Beijing 100816,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has created conditions and built bridges for greater openness in education and enhanced international talent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There is a deep foundation and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education opening. Over the years,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have carried out rich cooperation in traditional education fields such as univers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dditionally, they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expand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alents, and developing new digital talent training. Looking ahead,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should achieve higher-level, deeper and more influential institutional openness in the field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EAN; Luban Worksho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alent development; New digital talent development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吕伊雯
原标题:“***”倡议下扩大教育开放:东盟国家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4-05-13 12:00:00
时间:2024-05-13 1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