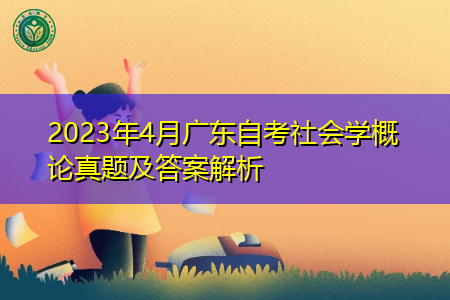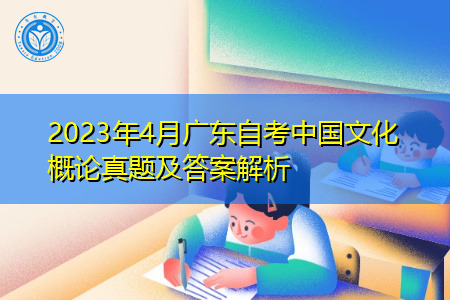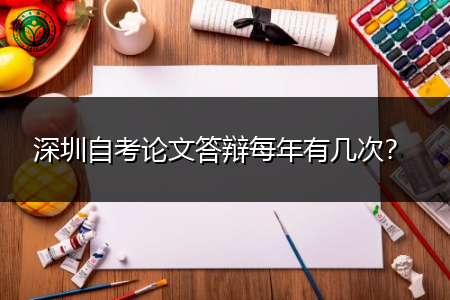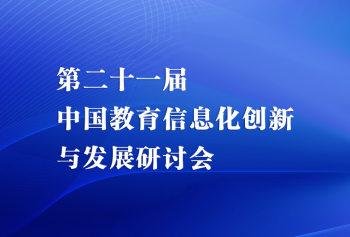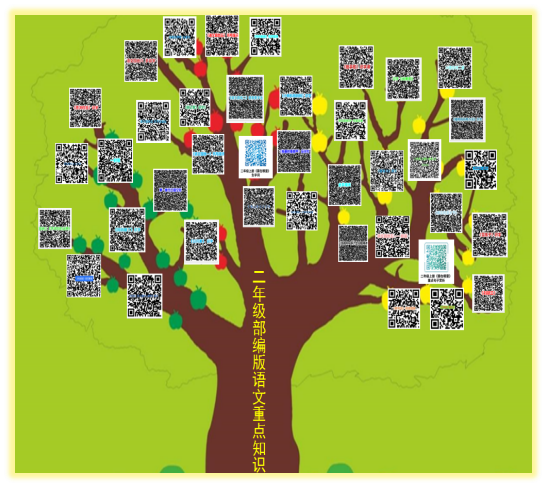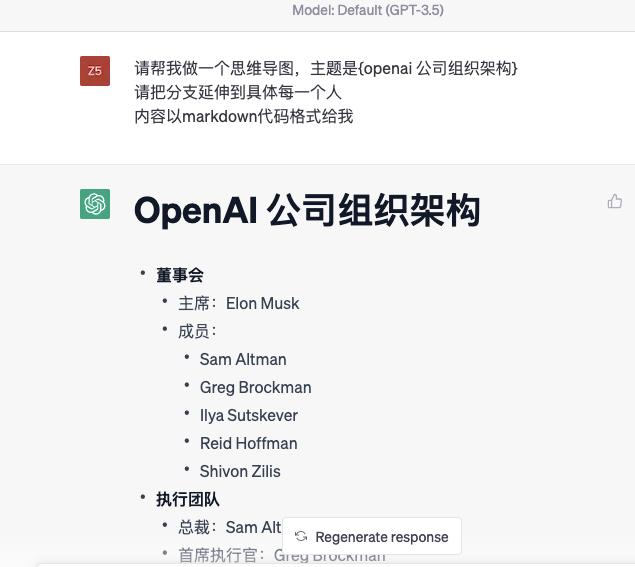摘 要:21世纪的挑战在中小学催生了全新的学习范式,STEM教育是应对的主要路径之一,STEM教师是其中重要的力量,因此有必要构建素养模型为教师的专业发展、专业实践赋能。文章在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小学STEM教育的总体认知框架,包括跨学科整合性、真实问题驱动、各学科平等性等基本假设,莱斯转换模型、STEM转换模型等参照系,经验学习、具体操作物、多元表征等理论框架和七个特征的概念框架;梳理了专业素养研究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概念,提出在情景专业主义视角下构建中小学教师专业素养模型;最后以美国州首席教育官员理事会提出的素养导向的教师核心教学标准模型为蓝本,综合总体STEM教育认知框架和专业素养理论,构建了包含学习者和学习、内容知识、教学实践、专业责任四大素养,12个亚素养的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并细化了指标体系。
关键词:中小学STEM教育;专业素养模型;跨学科整合性;莱斯转换模型;中小学STEM教师素养模型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方兆玉,法国高等科学技术与经济商业学院博士(巴黎 75015)、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教育》编辑部编辑(上海 200032)
基金项目:上海教科院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基础教育核心素养培养导向下教师跨学科能力建设及评价研究”(编号:BHA230151)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全球各国高度重视STEM教育,其推进STEM教育的紧迫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性产生威胁的环境和社会因素,同时,STEM教育受到“乌卡时代”①创新性危机的迫切需求和学科过度分化之后进入统整发展期的强力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STEM教育的意义已经超出帮助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测评中取得高分,或在STEM职业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更是为了回应时代的重大挑战。[1]
对于具有深厚的分科教育传统的中国中小学来说,STEM教育作为一个以跨学科整合性作为核心原则的知识领域[2],学术性和挑战性都很大。中小学STEM教师是应对挑战的核心力量,承担着多重关键角色:探索情景学习(situated learning),实施跨学科教学,提升科学与数学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创新素养。为中小学STEM教师构建作为坐标系的专业素养模型是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
二、中小学STEM教育总体认知框架
中小学STEM教育不是在上位理论框架指导下严密地进行应用和实践,而是从行动研究、扎根研究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规律、厘清核心要素、凝练有效特征,再进一步将其概念化和理论化。将中小学STEM教育视为一个新兴的知识领域,可以梳理出其独特的基本假设、参照系、理论框架和概念框架。藉此,中小学教师可以总体把握其核心要素和关键原则。
(一)基本假设
第一个基本假设是中小学STEM教育具有跨学科整合性。但通常STEM各子学科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需要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法与课堂策略进行展示,或支持学生自行探索。[3]第二个基本假设是中小学STEM教育是通过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来予以情境化的。第三个基本假设是中小学STEM教育支持学生21世纪技能的发展。第四个基本假设是中小学STEM教育各子学科间不存在主导学科、平行学科之分,应当同等看待。第五个基本假设是中小学STEM教育应当融入艺术、伦理、可持续发展等维度,避免落入唯技术中心主义的窠臼。[4]
(二)参照系
任何一个知识领域都有自己的参照系(reference),也就是韦伯所称的“理想型”。例如,物理学所创设的“无摩擦力学环境”,经济学提出的“一般均衡市场”。这些“理想型”并非现实本身,但抓住了核心要素和关键特征,为分析现实情况提供了起点和参照系。
莱斯转换模型(Lesh Translation Model)和STEM转换模型(STEM Translation Model)[5]可作为中小学STEM教育的参照系。
莱斯转换模型包含五个节点(见图1),分别是书面符号、口语表征、图像或图表符号、基于经验的隐喻、具体模型,节点之间的箭头代表不同的表征、符号内部或者之间的转换。转换是指某个概念从一种表征到另一种表征的联结或者重构。

图1 莱斯转换模型
例如,当学生先用文字描述了某个物体势能变化的状态,再用绘图的方式来展现该物体高度的变化时,就完成了从书面符号到图表或图像符号的转换。莱斯转换模型是一个理想型的、促进学生概念理解的思维框架,源于迪尼的多元具象表现理论,该理论扎根于其“内在规律通过厘定一个概念不同具象表现之间的联系才能得以揭示”的理念。[6]教师可以借助莱斯转换模型,要求学生在不同的表征之间进行转换,并通过观察学生在不同表征模式之间转换的流畅性,度量其概念理解的程度。
STEM转换模型(见图2)由莱斯转换模型衍生而来。如果将STEM视为一门“超级学科”,以贯通性(crosscutting)概念、实践或思维方式为“胶水”,将不同的STEM子学科粘合起来,那么各子学科就可以类比为莱斯转换模型的一个节点。数学、科学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就成为STEM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7]

图2 STEM转换模型
例如,“风涡轮设计”工程挑战是个综合性STEM问题,但学生一旦破题之后,就会“分支”到特定数学或科学原理的探究当中,如齿轮比率调整、叶片设计、风速计算,每个“分支”就体现出特定学科教学的特征。[8]如何促使学生感知并建立学科之间的联系?教师应鼓励学生运用STEM转换模型,在不同的子学科之间进行转换,即对于同一个STEM问题,变换问题解决的学科视角及其采用的概念、方法和技能,并通过相互对比、辨析异同、建立联系,创造性地整合出最优方案。这个过程能促使学生对各个学科的核心概念、对STEM跨学科大概念产生更细微的理解。将重点放在学科的联系和转换上,将各学科视为STEM“超级学科”的一种具象表现形式[9],更易理解STEM转换模型。
(三)理论框架
中小学STEM教育秉承社会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10],在这种理论框架下,学习不再是静态的、个体的,而是学习者在特定的情景下,通过与同伴、教师、工具、资源、环境的充分互动,共同凝练集体智慧,建构知识以及文化身份的过程。因此,中小学STEM教育不能只关注课程和教学法,而应该系统性地考虑如何创设有效学习环境。历史上,杜威、迪尼和莱斯三位学者通过持续的研究、讨论和阐述,为STEM学习环境的创设奠定了理论基础。[11]
1.核心概念或探究方式的整合
中小学STEM教育的核心是整合性,涉及各学科概念及探究方式的整合。在不同的问题情境下,不同学科有望整合出结构与功能、能量与物质、因果关系等贯通性概念。相比之下,探究方式的整合比较复杂,如科学中会用到科学探究,技术领域会用到计算思维,工程中会用到工程设计,数学中会用到演绎推理[12],它们是彼此独立、具有不同认知论基础的问题解决路径,其不同整合方式都有优势和劣势,对特定种类的问题具有特殊的适切性。而真实世界的问题又都是复杂、综合的,解决这些问题要求最大程度地发挥每种探究方式的优势。从这个视角出发,STEM的整合性不是简单地囊括各学科的内容、技能、思维方式,而是深入理解这些学科间的互动模式,及其互相支持和互补的方式。[13]
2.体现跨学科性
莱斯提出:“为了让学生为解决社会问题做好准备,有必要为他们提供机会,借助整合性STEM教育,通过丰富、有吸引力、深刻的学习经验来理解问题。”[14]杜威早在1899年就提出类似的观点:“分学科孤立的教学会弱化学科之间的联系,阻碍学生对他们希望洞察的现象或解决的问题形成整体的认识。”他进一步阐述:“启蒙之初,就为儿童引入泾渭分明的分科教学,会造成脱节和分化,而非协调与联系。在学校的人造环境之外,我们的生活经验都是整体化的,只有当我们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反思时,才能清晰地从中分解出各个学科。”[15]
莱斯以数学学科为例,指出数学教学掩盖了真实世界的情况,如教科书惯例化呈现和描述的图景在真实的场景中往往更复杂、情境化且综合多门学科。[16]如此一来,学生往往很难将学校所学与实际问题建立联系。因此,中小学STEM教育至关重要的是要在学科之间进行有意义的整合。
3.营造真实世界、问题导向的学习环境
为了减轻乃至根治分科教学带来的学习与生活脱节的弊病,杜威于1916年提出一条“另类”解决思路,即创设围绕专业(occupation)开展课程教学的学习环境,毕竟“唯一充分的专业训练就是真正地训练专业技能 ”。但杜威对专业或职业做出了不同于常规的界定,认为专业是一种有指向性的社会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下属的帮助,足以使个体对其他人产生切实可感的重要性。[17]杜威认为专业并非归属于某个行业领域,而是真实、吸引人、有成就感的社会活动。基于此,杜威提出学校教育应该模仿专业活动而开展。[18]
前文列举的“风涡轮设计”工程挑战,其驱动性问题是“如何在自己学校的操场上为风涡轮挑选一个最佳的安置场所”。在应对该挑战的过程中,学生探究风车设计的各种参数,观察、记录天气变化情况,并对相关的科学工程概念进行深度学习。[19]该问题情境是STEM整合性的,且该挑战是为了促进社区的公共利益,也具有真实世界问题导向的显著特征。
4.STEM学习的本质是社会性、合作性
杜威、迪尼和莱斯三位学者都认为学生应当进行合作学习,但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阐述。杜威认为,教育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也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功能。因此,学生应当作为社区中的成员,对相关议题采取行动。杜威构想中的学生行动应当是社区行动,要求学生作为学习共同体中的成员进行协作。[20]而莱斯的推导逻辑是,学校外的真实生产、生活中的跨学科问题都是由分属不同专业领域的人组成团队来解决的,因此,学生也应该以团队的形式来解决问题。[21]迪尼支持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在于其认为学习是社会性的。[22]
总体而言,三位学者分别从公民素养、专业实践、学习本质三个角度进行论证,殊途同归于“合作学习”这一交汇点。
5.引入个人经验
杜威和莱斯认为学生将个人经验带入到真实情境中的学习非常重要。例如,在“风涡轮设计”案例中,正是因为将问题情境设置在学生所在的学校,学术问题得以转换为个人和社区的有效行动,成为杜威所描述的“能够为他人服务的活动,并因服务成就来获得个人权力”。[23]这些活动也符合莱斯所提出的“真实性原则”[24],即学生基于对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延展就能理解其所处情境的活动。在学校之外,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涉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因此,在中小学STEM教育中为学生创设的挑战性问题也应当体现这些特征。
相较而言,迪尼则更注重个人经验的引入本身。他认为只要学生能够在学习活动和真实经验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学习活动可以在缺乏真实情境创设的情况下进行。对于数学学习与真实经验之间的关系,迪尼认为:“数学知识是生活经验中美妙的、规律的、结构化的关系的晶体化(crystallization,即显性的固化)。这些关系是从与真实生活实际接触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25]拓展迪尼的观点,可以发现:除了数学规律,学生还能够从感知真实世界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科学概念。例如,儿童在移动不同尺寸的物体时更深刻地理解“力与运动”的概念。迪尼认为,与个人经验建立联系不仅在于将学校学习和学生生活联系起来,更在于帮助学生抽象出数学模型、规律、结构,这个过程对学习至关重要。为此,他表示:“教师的角色就是将学生‘带入’合适的经验,来加速他们对相关概念的理解。”[26]
三位学者都认同“概念理解扎根于真实生活经验”。迪尼称之为具身知识(embodiment knowledge)[27],即知识和能力是围绕真实经验来组织的。杜威对专业也有类似论述:“专业既是磁石,也是胶水,对于知识的组织(结构化)至关重要……而且专业诉诸于真实需要,在应用中一直被表达,一直被重新调整,因此永远不会僵化过时。”[28]可以说,专业知识是活化的、动态发展的、以专业实践为核心组织的。莱斯认为,该观点是情景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的先驱,并认为:“情境(context)至关重要,因为学习者的心智模型植根于具体情境”。[29]
6.概念抽象化需要多元表征
中小学STEM教育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多元表征(multiple representations)。关于经验支持学习的机制,三位学者的观点大体相似,但略有不同。杜威解释了专业对于学习的影响,并提到了两个核心原则:连续性与互动性。连续性是指学生当下的体验会对其未来的经历产生影响;互动性是指当下所处的情境会影响其此时此刻的体验。通过这两个机制,所有经验都获得了教育意义,只是有些经验支持未来发展而另外一些则会产生阻力。[30]为此,杜威提出,教师应当遴选合适的当下经验,以帮助学生有成效、创造性地驾驭生活。但杜威并没有就哪些特定的活动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学生未来哪方面的表现做出进一步论述。
迪尼和莱斯则深入检视了哪些特定的学习活动及其之间的联系能够促进学生思维的一般化和抽象化。[31]迪尼植根于对中小学生的丰富研究,提出对于学生而言,将学校的物理学习与真实的物理现象或物体建立联系至关重要。这些物体也被称为具体操作物(concrete manipulatives),因为学生必须有机会实质性地操作,才能对其结构进行深入探究。迪尼也认识到,仅仅对这些具体操作物进行探索还远远不够,因为从同一类经验中无法抽象出规律。他指出概念并非从具体的物体当中抽离出来,而是在将该物体与其他具体操作物进行对比、分析以及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被发掘出来。[32]
基于此,迪尼提出了将学习活动结构化,以便导向概念发展和抽象化的四条原则:建构原则、动态原则、数学可变性原则和感知可变性原则。建构原则是指儿童的知识必须建构在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之上。动态原则致力于让学生去发现变化中系统的规律。如果想让儿童发现建构物隐藏的规律,必须让该系统经历变化,才能使相关概念或原理变得“可视化”。例如,如果不去改变一个风涡轮的叶片角度、齿轮的个数及其排布方式,儿童就不会发现这些因素对于风涡轮功率的影响。此外,为了促使儿童的概念进一步向精微、成熟发展,教学活动还必须提供变化的数学和感觉参数。对于任何给定的具体经验或者具体操作物,都有许多变量可以调整。数学可变性原则要求对于某个变量进行系统性的操控,以便暴露内在规律。感知可变性,也称为多元具身表现,是指每个概念都应以尽可能不同的方式呈现。具身表现的方式于感官而言,应该尽可能地充满变化,才能将学生的思维导向同一个概念的抽象化。例如,对风涡轮的齿轮个数与功率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就是“比率”(ratio)这个概念的具象表现。如果不经过对比,学生很容易将比率视为齿轮的一个特征。学生必须通过与其他的具象表现或表征模式进行综合比较,才能够抽象出概念。
一个STEM课程单元往往具有多个核心概念,如果围绕某个概念设计了太多的具身表现,虽然创造了以多元表征去探索、抽象该概念的机会,但会造成整个单元连续性的中断,或弱化其他概念。孰优孰劣,如何取舍?迪尼认为具体操作物是数学课堂的必备[33],莱斯则提出了一个前面提到的、如今已被广泛使用的转换模型。
莱斯转换模型不仅是促进概念理解的模型,也是指导STEM教学的框架。为了促进学生对大概念的理解,STEM教师可以依据“促使学生在不同的表征模式进行转换”的原则来设计学习任务和活动。例如,在分析风车的叶片构型时,学生可以用图表和书面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查规划、记录观察结果,并参与小组活动,通过口头表达的方式阐释构型、功率、比例等核心概念。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讲述相关的生活经验,并用不同的隐喻(感性描述或形象的比喻)来表征不同强度的风。[34]
从杜威的经验学习到迪尼的多元具身体现,再到莱斯STEM转换模型,支撑STEM教育的理论基础一直在动态发展。经验学习、具体操作物、多元表征是教育实践界从三位学者那里继承而来并践行于课堂的三个核心理念。[35]将其与STEM教育研究的成果以及一线课堂的教育实践进行充分整合,提炼特征、要素、维度,可以构建出指导中小学STEM教与学的概念框架。
(四)概念框架
将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具体化、操作化,构建出中小学STEM教育概念框架,包含整合的本质、工程的角色、STEM职业认知三个维度下的七个特征。[36]
1.特征一:聚焦真实世界问题
真实世界问题的遴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许多因素都与学生认知性和情感性的学习成果密切相关。学生个人的种族、性别、兴趣、家庭背景、学术特长会对其偏好的问题种类、范围或情境产生影响。[37]例如,男生更倾向于参与机器人、无人机、机械类产品的制作,而女生更倾向于情感陪伴类应用、四季穿衣指南、校园“零碳日”倡议活动等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的STEM任务。真实问题还必须与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对齐,确保学习活动能够深化学生的概念理解。情境化是将学术内容精心嵌入到一个真实问题情境中的过程;概念化是从日常生活、自然现象、棘手难题出发去提取相应的学科概念、研究方法为我所用的过程。遴选真实问题必须考虑到学生概念学习的潜力。
2.特征二:工程设计的中心地位
在中小学STEM课程中,教师须确保学生有机会完整经历工程设计构思、制作、测试的过程,让学生评估设计作品,并基于采集到的效能数据以及科学原理,依据确定的标准,进行迭代优化。工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成本、材料、功能等技术因素,还要考虑其产生的社会和伦理影响。[38]
教师须确保学生带着对相关科学概念、工程设计流程、技术使用方法的深刻理解参与到作品或方案设计中,才能体现学习内容与真实生产生活的深度整合。这就要求学生对其工程设计流程进行持续反思和基于证据的论证,不断将一般性科学原理与情境性的条件、参数、约束乃至社会伦理规则进行协调、匹配,得出特定情境之下最优设计方案的同时,提炼一般性知识情境化应用的策略。
3.特征三:背景整合
作为背景的真实世界问题和工程实践挑战必须与STEM内容充分整合,而非仅提供一个情境。过去十几年中,工程课程、创客空间和数字制作实验室在美国K-12学校“泛滥”。相关研究表明,那些参与了动手实践、基于项目的工程课程的学生,对数学和科学知识所学甚少,症结就在于学习内容与项目活动之间缺乏显性、清晰的联系。[39]有学者在系统性文献综述中提到,在154篇与中小学STEM教育相关的论文中,近40%的研究将课程目标聚焦于学生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期望,而非学习特定的概念。[40]
为了强化工程设计活动与科学概念学习之间的联系,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在整个迭代设计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应用科学、数学知识,搜集测试原型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数据并进行分析,有理有据地推动设计工作的进展。
4.特征四:内容整合
STEM教育中最关键的是内容整合,包括科学子学科之间的横向整合、从科学到工程到技术的纵向整合。教师必须为学生示范跨学科整合的方法、策略或模型,如STEM转换模型,使学科之间、问题情境和学术学习之间的整合显性化,必要时教师应当提供知识整合工具,采用一些概念化思维的学习支架或提问的策略,促使学生对整合性质产生深度理解。
教师还可以加入非STEM学科的内容来扩展学生的学习体验,或采用社会性科学议题教学法[41],开发更体现人文关怀的设计方案。
5.特征五:STEM专业实践
中小学STEM教育为学生提供机会参与真实的STEM专业实践,或在创设的模拟问题情境中设计针对特定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工程问题天然具有综合性、多面向性,具有多个解决方案。教师应当给予学生自主权,让他们勾勒自己的破题路径。
教师还应培养学生的数据素养。数据实践是STEM从业者知识建构和专业工作的核心,包括数据的创建、采集、处理、分析和可视化。[42]论证是科学和工程领域共同的核心实践。研究表明,K-12学生使用证据和科学概念来为其工程设计进行辩护的能力较弱。通常情况下,学生更多聚焦于成本和材料,不会自发地使用科学或数学概念来为自己的工程设计方案或作品进行解释。因此,将基于证据的论证融入到中小学STEM课程中,对为学生提供支架和建立科学、数学概念与工程挑战之间的联系必不可少。[43]
6.特征六:21世纪技能导向
真实世界中的工程设计问题往往是模糊、多义、劣构的(没有现成的解决答案,没有精确界定的标准流程),为学生提升21世纪技能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当学生参与到迭代的工程设计过程中时,教师应对他们进行分组,以支持合作、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高阶认知任务的完成。[44]教师还必须精心策划、组织、实施小组学习活动,保证公平参与,推进工程设计的顺利实施。
7.特征七:STEM相关职业认知
在中小学STEM教育中,教师应当介绍和描述与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STEM职业,以激发学生兴趣。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对STEM的兴趣、态度和身份认同是STEM学科持续性深造的预测性因素。[45]另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到八年级末已经形成对STEM职业的兴趣和期望。[46]具体的教学策略方面,虽然教师在引导学生开发工程设计方案的过程中,也会渗透STEM身份、职业等信息,但是依然有必要对STEM相关职业进行显性的讨论,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特定的职业机会,使其将这些职业要求与自己的学术兴趣对齐。
三、素养运动发展中的专业素养研究
(一)专业素养的内涵与影响因素的变迁
1.专业素养与效能动机
1959年,能力/素养(competence)概念首次通过怀特的著作引入到心理学有关动机的研究中,随后成为一个解释人类行为的关键构念(conception,理论化的概念)。在怀特的定义中,素养是有机体与环境进行有效互动的能力,人类的专业素养并非自然成熟,而是通过长时间、多阶段的学习才能缓慢获得。[47]
值得注意的是,在怀特的解释框架中,素养是一个动机性(motivational)的概念,他称之为“成为有能力的专业人士”的动机,即效能(efficant)。这种推理逻辑在素养运动以及21世纪技能、核心素养教育改革的话语中盛行:一般来说,学生、儿童和专业人士都有理解复杂现象、掌握特定技能、在特定环境中有效行使功能的动机。[48]班杜拉提出,当一个问题很复杂或一个任务情境要求很高时,能够理解问题并且在特定情境下有效地决策和行动的人往往会变得十分自信。在此过程中,他们得到了内在奖励,获得自我效能感。[49]
1916年,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中强调了职业、专业能力的重要性,用到的术语是工业能力(industrial competency)。他说:“人的生活离不开生存资料,民主社会的标准要求我们都能发展出选择或创造自己职业的能力……将职业或专业素养与日常作为良好公民的素养进行绝对区分当然有失武断,然而在满足即时工作的精熟度和对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洞见之间,在高效执行他人计划和谋划与启动、推行自己的倡议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能力差距。”[50]
结合杜威所提倡的专业或职业素养,研究者将专业素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工作、职位、组织环境或任务情境下,一般性、整合性、内化了的产生有效、有价值、可持续表现的能力,包括问题解决、实现创新和引领变革”。[51]
2.智力评价与素养评估
在专业素养的研究历史上,智力也是核心概念。人们往往认为,智商越高的人在专业或职业领域中的表现越好。由此,很多工作或职位的能力倾向测试被设定为评估候选人的智力。一方面,多项实证研究发现,智商测试分数和候选人在实际工作当中的表现并没有太大联系;另一方面,受到维度单一(虽然后由加德纳扩展到多元智能理论)的批判,职业能力评估的焦点逐渐转向素养评估。[52]
1973年,麦克兰德提出了素养评估的六项原则[53]:原则一,为评价标准提供可参照的样本;原则二,对候选人知识或技能习得的情况进行动态测试;原则三,公开、明确地阐释达到测试中所要求的职业或岗位特征的提升路径;原则四,专业素养被划分为若干亚素养,为每个亚素养提供基于真实职业表现的样本;原则五,评估不只依赖于对清晰界定问题的应答,还包含模糊指令条件下高仿真实世界劣构问题的情境题项;原则六,题项样本应聚焦于构想典型的行业领域操作流程,这类题项比微小技能的测试更能够引发高阶思考,评价候选人的一般化能力或概述能力。这些原则直接影响其后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习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3.专业表现与专业素养调控
1978年,吉尔伯特在《人类素养:提升有价值的表现》一书中,将专业素养和专业表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三个支撑这一论断的定理。[54]
第一个定理是:专业表现是结果导向行为产生的效应,人类素养是有价值表现的函数,即有价值的成就除以为该行为付出的成本。第二个定理是:专业表现本身并非专业素养,专业素养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特定社会、特定情境、特定领域中,人们对表现的相对评价。第三个定理是管理理论,是与专业人士的遴选、工作环境的安排、绩效标准的确定、工作表现的监督、激励和问题分析相关的规则。吉尔伯特强调,为了让专业人士完成高标准的专业表现,需要特定的专业素养、一整套专业行为,以及为有价值专业表现提供支持的环境。
总之,怀特、麦克兰德、吉尔伯特为理解专业素养及相关概念提供了“棱镜”,籍此可洞悉专业素养与动机、素养评估、专业表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构建专业素养模型,划分专业发展阶段
1.任务导向与一般化的专业素养模型
专业素养研究伴随着素养运动而兴起。格兰特[55]指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脱节是素养运动的起因。当时,行业协会或专业组织开始对高校提出绩效要求,并开发出求职者或资格证书候选人要遵从的素养框架。高校开始重新调整、设计课程,融入行业协会、专业组织及企业工业所看重的知识和技能。这就要求构建专业素养模型。
1994年,罗斯提出了涵括多个专业领域从业者的核心素养模型,包括领导者、经理、专业工作者、销售和市场人员、财务人员、信息技术人员、人力资源顾问等,并开发了配套的素养工具。[56]1996年,托马逊等人为经理开发了一个包含8个维度的专业能力框架。[57]
这些都是任务导向的专业素养的典型代表,包含所在领域的诸多细节。但早在1982年,波亚缇斯就从“有效表现”理念出发,为管理人员提出了一个一般化专业素养模型,并把专业素养界定为“一系列导向在某项工作中的有效或卓越表现的支持性的人格特征”,包括动机、特点、技能,某人自我形象或社会角色的侧面或者是一系列知识。[58]
美国培训与发展学会1989年提出一个统一的素养模型,包含一般/基础素养与领域素养,为专业人士自我评估和基于工作场所学习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考系和评估框架。[59]
一般/基础素养和任务导向的领域素养中,专业素养都由若干个亚素养组成,亚素养是能在真实的专业情境下使用的一系列知识、技能、态度的有机组合。例如,调查犯罪现场,需要法医出具一份对某个证据的脱氧核糖核酸(DNA)报告。此任务既要求知识(学科知识)、技能(运用专业的设备和工具),也需要态度(精确性、正直、抗压),三要素共同构成了这名法医的专业素养。[60]
中小学教师是适用任务导向,还是一般化的专业素养模型?从实践导向的专业人员的视角出发,专业素养是专业工作者不可或缺的行为表现,若缺失,则无法在自己的专业场域中有效地行使功能。因此,必要的细节描述和领域专属的知识技能对于中小学教师的素养模型来说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任务导向更加适切。
2.专业发展阶段
构建了专业素养模型后,还要划分专业发展阶段,为专业学习提供洞察。1986年,德累菲斯提出了高技能型人员专业发展的五阶段:新手、进阶新手、胜任者、精通者、专家。[61]但由于概念的重合、交叉或模糊性,莫德提出了一个专业发展阶段理论:第一个阶段为“无知”,通过直接教导才能够行动的新手;第二个阶段为“新生”,能够在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学徒;第三个阶段为“胜任者”,能够独立工作,是专业主义最基础的层级;第四个阶段为“优秀”,在专业领域表现卓越,已成为专业领域的专家或资深从业者;第五个阶段为“卓越”,具有该行业领域卓越的才能和高超的表现,是组织内、行业内或整个社会的明星人物。[62]
(三)理论视角进化史:从行为主义—功能主义、整合职业主义到情景专业主义
深究不同专业素养模型的底层逻辑,可划分为三条学理路径。第一条路径是行为主义—功能主义(Behaviouristic Functionalism)[63],在这个理论视角下,专业素养模型强调的是确定真实表现与理想能力之间的差距,由此导向对专业素养进行细分并逐个训练的培训方式,接近于掌握学习的思路。可能的弊端是碎片化学习以及对微小技能训练的过分倚重。
第二条路径是整合职业主义(Integrated Occupationalism)[64]。整合职业主义素养模型的核心是职业、角色或特定领域所需的综合素养,而非任务或活动。因此,基于素养的教育模式会强调知识、技能和态度应当在课程、教学、学习和测试中进行整合性规划、设计与实施,而专业质量保障框架则努力将核心角色、工作场域、工作流程与专业素养联系起来。
第三条路径是情景专业主义(Situated Professionalism)。[65]在该理论视角下,专业素养只有在特定情境当中才能体现意义,并没有独立于情境之外抽象的素养可言,这与情景认知和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观点相契合,对专业教育和专业发展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结果是真实性学习、实践共同体的广泛流行。但该路径经常被批判易于陷入整体主义,即当谈论的都是人们跨领域的一般性能力时,特定领域、特定专业素养的细节就难以得到充分表现,因此只能对个人的专业发展起到指导作用,而无法用于专业资质鉴定。[66]
综合分析下来,情景专业主义是最适合中小学教师素养模型的一种理论视角,因为它在强调整合性发展具有领域属性的专业角色的同时,也凸显了专业实践与专业情境的社会互动。
四、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
(一)21世纪核心素养教学的教师素养模型
2013年,美国州首席教育官员理事会(CCSSO)推出了核心教学标准模型(Model Core Teaching Standards,MCTS),是包含四个领域的中小学教师专业素养模型,包括学习者和学习、内容知识、教学实践、专业责任,进一步细分为10个亚领域,包括学习者发展、学习差异、学习环境、内容知识、内容应用、评估、教学设计、教学策略、专业发展和合乎伦理的实践、领导力与合作。[67]
MCTS体现了素养教学的明显特征,如学习者和学习包含了学习者发展、学习差异和学习环境三个亚领域,体现出对学生发育、心智成长、学习规律的尊重;采用情境化、任务导向、合作学习等创新教学方式,融入数字技术,对课程、教学法、数字空间、物理空间进行系统设计,要求教师熟练掌握学习科学规律,进行目标导向的学习体验设计以及学习环境创建。
从MCTS的结构来看,四个素养领域都是知识、态度、专业表现的有机融合,在不断地与专业情境以及其中的其他主体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获得意义、实现价值;并根据多元情境和互动对象的不同而动态演变。专业素养模型中不仅包含体现静态教师角色的内容知识、教学实践,也包含嵌入在专业情境中的互动主体——学习与学习者以及专业情境下长期发展的专业责任,完全契合“专业实践与专业情境相互建构”的情景专业主义理论视角。
(二)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
中小学STEM教育以21世纪技能为培养目标。[68]在情景专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倡导21世纪素养教学的MCTS为“骨架”,以中小学STEM教育的总体认知框架为“血肉”,笔者初步构建出包含学习者和学习、内容知识、教学实践、专业责任四大素养和12个亚素养的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见图3)。

图3 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
学习者和学习包含学习者发展、学习差异、学习环境3个亚素养[69];内容知识包含元认知、STEM知识、知识应用3个亚素养;教学实践包含教学评估、课程设计、教学法与教学策略3个亚素养;专业责任包含专业发展、STEM伦理、领导力与合作3个亚素养。
确定素养和亚素养之后,结合前文提到的中小学STEM教育总体认知框架,笔者进一步细化了典型行为表现,构建了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指标体系

(接上表)

综上,本文在对中小学STEM教育相关的理论基础和概念框架进行总结提炼的基础上,以素养导向的MCTS为蓝本,构建了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并对大量文献中的优秀案例进行剖析,萃取每个亚素养的若干教师典型行为表现,构建细化的指标体系。一方面为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指引,另一方面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注释:
①“乌卡时代”意指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具有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的时代,四个单词的首字母组成“VUCA”,音译为“乌卡”。
参考文献:
[1]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EB/OL].(2016-05-04)[2024-03-05].http://www.p21.org/about-us/p21-framework.
[2]方兆玉.素养本位的STEM教育:理念、目标与实践模式——美国、法国、新加坡比较研究[J].世界教育信息,2024,37(1):60-70.
[3]KIM K. The creativity crisis: the decrease in creative thinking scores on the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11, 23(4): 285-295.
[4]WALKER III W S, MOORE T J, GUZEY S S, et al. Frameworks to develop integrated STEM curricula[J]. K-12 STEM education, 2018, 4(2): 331-339.
[5][6][7][29]GLANCY A W, MOORE T J.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effective STEM learning environments[C]. West Lafayet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2013.
[8]CRAMER K. Using a translation model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classroom instruction[M] // RICHARD A J L, DOERR H M (Eds). Beyond constructivism: models and modeling perspectives on mathematics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449-463.
[9]LESH R A, POST T R, BEHR M J. Dienes revisited: multiple embodiments in computer environments[M] // WIRSUP I, STREIT R (Eds). Development in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Reston, V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87:647-680.
[10]BROWN J S, COLLINS A, DUGUID S. Situated cognition and the culture of learning[J].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989, 18(1): 32-42.
[11][12][13][35][36][37][38]ROEHRIG G H, DARE E A, ELLIS J A, et al. Beyond the basics: a detailed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STEM[J]. 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2021, 3(11):2-22.
[14][16][24]LESH R A, HOOVER M, HOLE B, et al. Principles for developing thought-revealing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M] // KELLY A, LESH R A(Eds). Research design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591-646.
[15]DEWEY J. Lectures in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899[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33-52.
[17][18][20][21][22]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M]. New York: Macmillan, 1916:12-25.
[19]CAPOBIANCO B M, RUPP M. STEM teachers’ planned and enacted attempts at implementing engineering design-based instruction[J]. School science mathematics, 2014, 114(6): 258-270.
[23][28][30]DEWEY J.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M].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1938:57-72.
[25]LESH R A, DOERR H M. Foundations of a models and modeling perspective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learning, and problem solving[M] // LESH R A, DOERR H M(Eds). Beyond constructivism: models and modeling perspectives on mathematics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and teach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3:3-33.
[26][27]DIENES Z P. Building up mathematics[M]. London: Hutchinson Educational, 1960:10-15.
[31]LESH R A, HAREL G. Problem solving, modeling, and local conceptual development[J].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learning, 2003, 5(2): 157-189.
[32][33]DIENES Z P, GOLDING E W. Approach to modern mathematics[M].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1:6-52.
[34]LESH R A, ZAWOJEWSKI J. Problem solving and modeling[M] // LESTER F K (Ed). Secon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2007:763-804.
[39]ADAMS B S, FREEMAN A, GIESINGER H C, et al. NMC/CoSN horizon report: 2016 K-12 edition[M]. Austin: The New Media Consortium, 2016:11-45.
[40]TAKEUCHI M A, SENGUPTA P, SHANAHAN M C, et al. Transdisciplinarity in STEM education: a critical review[J]. 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2020, 56(2): 213-253.
[41]ROEHRIG G H, KERATITHAMKUL K, HIWATIG B. Intersections of integrated STEM and socio-scientific issues[M]//POWELL W(Ed). Socioscientific issues based instruction for scientific literacy development. Hershey: IGI Global, 2020:121-176.
[42]BECKER N M, RUPP C A, BRANDRIET A. Engaging students in analyzing and interpreting data to construct mathematical models: an analysis of students’ reasoning in a method of initial rates task[J]. Chemistr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17,18(4):798-810.
[43][74]ASUNDA P A, MATIVO J. Integrated STEM: a new primer for teaching technology education[J].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teacher, 2017, 76(5): 14-19.
[44]AMINGER W, HOUGH S, ROBERTS S A, et al. Preservice secondary science teachers’ implementation of an NGSS practice: using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J]. Journal of science teacher education, 2021,32(2):188-209.
[45][46]KITCHEN J A, SONNERT G, SADLER P M. The impact of college-and university-run high school summer programs on students’end of high school STEM career aspirations[J]. Science education, 2018, 102(3): 529-547.
[47][51][60][62][63]MULDER M. Conception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M]//BILLETT S, HARTEIS C, GRUBER H(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professional and practice-based learning. Dordrecht: Springer, 2014:107-137.
[48][49]WHITE R W. Motivation reconsidered: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59, 66(5): 297-333.
[50]DEWEY J.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M]. New York: Macmillan, 1916:3-42.
[52]GARDNER H. Frames of mind: 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60-72.
[53]MCLELLAND D C.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3, 28(1): 423-447.
[54]GILBERT T F. Human competence: engineering worthy performance[M].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60-110.
[55]RIESMAN D. Society’s demand for competence[M]// GRANT G, et al. On competenc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ompetence-based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1979:18-65.
[56]ROSIER R. Competency model handbook, Volume I-IV[M]. Lexington: Linkage, 1994:72-90.
[57]QUINN R E, FAERMAN S F, THOMPSON M P, et al. Becoming a master manager: a competency framework-second edition[M]. New York: Wiley, 1996:43-67.
[58]BOYATZIS R E. The competent manager: a model for effective performance[M]. New York: Wiley, 1982:65-70.
[59]ASTD. ASTD competency model[M]. Alexandria: 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 Development, 2013:70-93.
[61]DREYFUS H L, DREYFUS S E.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ienc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55-90.
[64]OONK C, BEERS P J, WESSELINK R, et al. Roles and tasks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regional atelier[C]// DEITMER L, GESSLER M, MANNING S(Eds). Proceedings ofthe ECER VETNET Conference 2011 ‘Urban Education’. Berlin: Wissenschafts forum Bildung und Gesellschaft, 2011.
[65][66]WENGER E, MCDERMOTT R, SNYDER W M. Cultivat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M]. Harvard: 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2:62-79.
[67][69]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Interstate Teacher Assessment and Support Consortium in TASC Model Core Teaching Standards and learning progressions for teachers 1.0: a resource for ongoing teacher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C: Author, 2013:8-57.
[68]DARE E A, KERATITHAMKUL K, HIWATIG B M, et al. Beyond content: the role of STEM disciplines, real-world problems, 21st century skills, and STEM careers within science teachers’ conceptions of integrated STEM education[J]. Education sciences, 2021, 11(11): 737.
[70]BLACKLEY S, SHEFFIELD R, MAYNARD N, et al. Makerspace and reflective practice: advancing pre-service teachers in STEM education[J]. Australi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17, 42(3): 22-37.
[71]BILLINGTON B, BRITSCH B, KARL R, et al. SciGirls Seven-how to engage girls in STEM[EB/OL]. (2013)[2024-03-10]. http://www.scigirlsconnect.org/scigirls.
[72]Inquiry-based science education competencies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a literature study and critical review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12,34(17):2-15.
[73]BERLAND L K, MCNEILL K L. A learning progression for scientific argumentation: understanding student work and designing supportive instructional contexts[J]. Science education, 2010, 94(5): 765-793.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K-12 STEM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odel
FANG Zhaoyu1,2
(1.Institut Suprieur des Sciences, Techniques et Economie Commerciales, Paris 75015, France;
2.Shanghai Education Magazine, Shanghai Educational Press Group,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challeng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model of learning, and K-12 STEM education is the major approach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hile K-12 STEM teachers make the cornerstone workforce in this regard. Therefore, it’s imperative to formulate a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ramework to empower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studi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overall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K-12 STEM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interdisciplinary, real-world problems, equality for S-T-E-M), benchmarks or reference (Lesh Translation Model, STEM Translation Model), 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eriential Learning, concrete manipulatives,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s well as conceptual framework (7 characteristics). Secondly, it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researches in order to extract critical concepts. In light of which, we have decided to adopt Situated Professionalism a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construct K-12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odel. Lastly, it takes MCTS which initiated by US CCSSO as blueprint, enriched by the overall STEM education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construct the STEM-KDP K-12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framework, including four competencies, namely Learning and Learner, Content Knowledge, Teaching 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lso, 12 sub-competencies as well as a variety of indicators are proposed.
Keywords:K-12 STEM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model; Interdisciplinarity; Lesh translation model; K-12 teachers’ competence model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吕伊雯
原标题:中小学STEM教师专业素养模型的理论建构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稿源:《世界教育信息》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4-11-19 12:00:00
时间:2024-11-19 1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