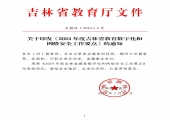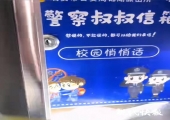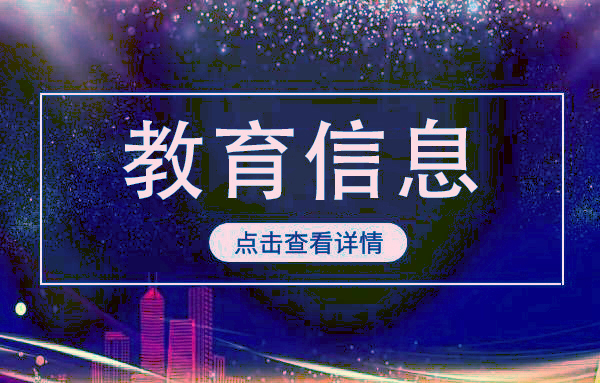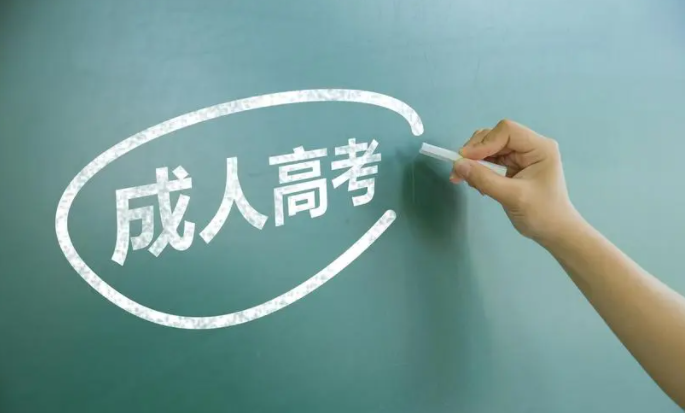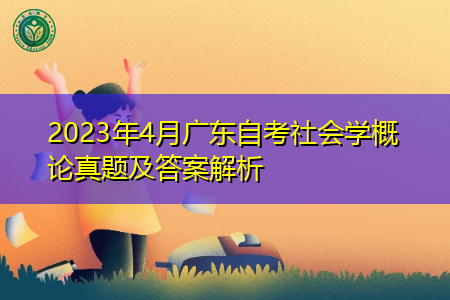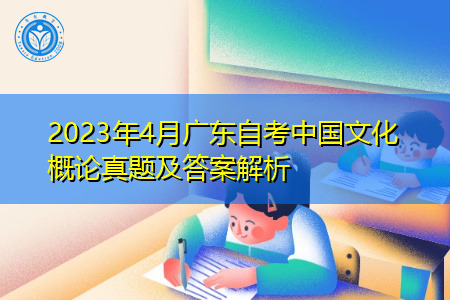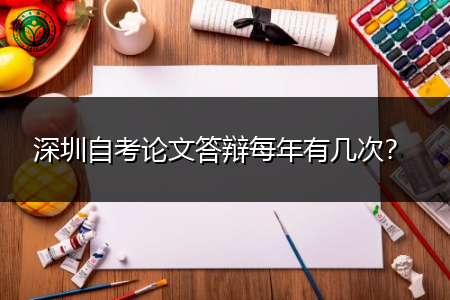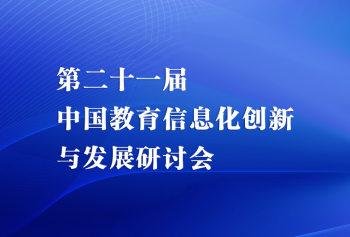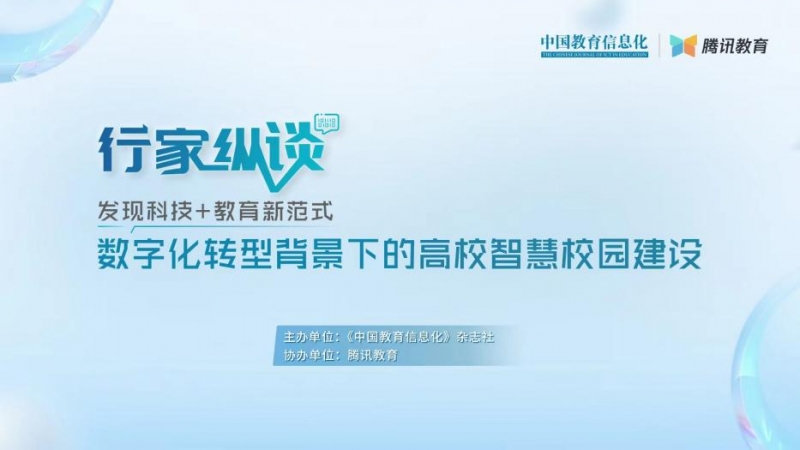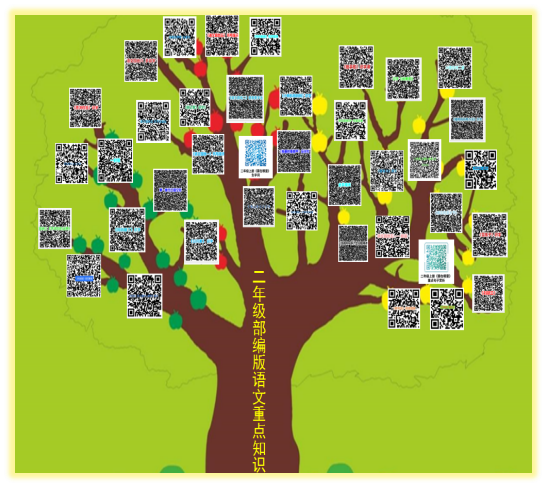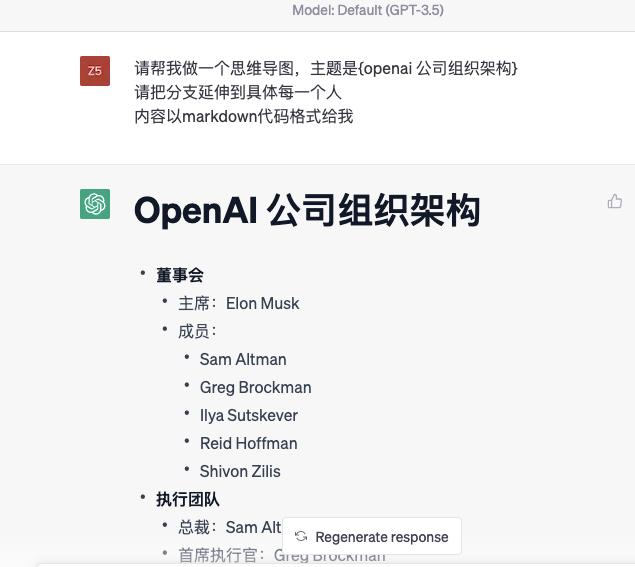摘 要: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化解当下学校管理困境,重塑学校管理生态,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前沿问题。然而,当下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遭遇了管理要素协同失灵、管理流程路径依赖、管理结构趋同僵化等问题。为此,需要统筹规划、系统推进,从构建数字化转型协同治理机制、以数字化技术驱动管理流程再造、塑造数字化管理网络结构组织等方面来推动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助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结构重塑;网络组织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志码:A
作者简介:林秋贵,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510631)
随着量子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数字化给整个社会以及个人生活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规则变化与环境变迁实时、实地地发生着。在教育领域,数字思维和数字化存在逐渐变为现实。在变化中寻找契机,推动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未来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数字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注重战略层面的变革,如美国的《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 NETP)、欧盟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德国的《中小学数字化公约》(Der Digital Pakt Schule 2019-2024)、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Le Plan Numérique pourl’?魪ducation)等。推动学校数字化转型发展也已经成为我国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然而,在数字化时代的冲击下,学校管理不仅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与技术机遇,也存在诸多复杂性挑战。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化解当下学校的管理困境,重塑学校管理生态,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前沿问题。
一、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基本内涵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核心主线。高质量发展需要持续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学校管理发展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手段,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和推动力。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数据量化管理对象与管理行为,实现管理职能与管理目标,重塑学校管理模式并以此驱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管理活动。本质上,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还是管理,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的内涵特征。
(一)要素协同是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前提
要素是管理的基本单元,在教育中即指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中的人、财、物、事、信息、媒介等。全要素协同是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前提。在数字化时代,万物皆数、万物互联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数字为基础,网络为形态,这是新时代的两大特性。任何要素都可以视为数字,要素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变成一种在线的数字化链接关系。要素协同就是应用数字技术,通过技术驱动、激发全要素活力,将管理要素中的人、财、物、事、信息、媒介等抽象转化为符号或数据,进而重构为互联协同的综合集成系统。这有助于打破传统的要素配置方式,打破学校职能部门之间和数据之间的壁垒,推动跨部门数据互联和系统互通,推动要素的协作化开发、集约化整合和高效化利用,提高全要素效能[1]。
(二)流程再造是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需求
从数字技术视角来看,管理本质上就是数字管理,管理要素被转化为数字之后,彼此之间呈现为纵横贯通的网络关系。由于网络技术具有离散、移动与高效的特征,学校师生员工差异化、个性化的新需求将不断被激发。面对分散的网络节点,要打通整个教育教学业务流程,做好学校管理中计划、组织、执行、协调、监督和控制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实现一体化运行是关键。流程再造就是通过数字技术驱动重构传统的过程管理逻辑,在实际操作中,即根据师生员工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基于教育教学情景对业务流程进行再造,打破“信息孤岛”现象,让学校管理系统形成价值链并按照“链”的特征实施业务流程管理[2]。相比于传统管理业务流程,数字赋能之后的管理流程会体现出即时性、自动性和远程性等特征,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服务效率。
(三)结构重塑成为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
数字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深度应用,其最大挑战来自学校行政组织结构和层级的裂变。数字技术为学校行政组织结构重塑提供了可能。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使得管理内部信息的搜集、传递、分析与处理等工作可由人工智能替代。数据的流动不必再遵循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等级阶层,就可实现部门与部门、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学校师生员工之间形成融合的合作伙伴关系,彼此之间平等、互相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时代科层制、简单的线性链条转向多方参与的网状模式,知识民主、去中心化趋势呈现。另一方面,这种无差别、无层次的数据流动方式极大地颠覆了传统的金字塔型管理模式,驱动管理规则重塑,管理层级的缩短和管理幅度的扩展逐渐成为共识。学校行政组织结构逐渐由以指令为主的科层管理范式向数据驱动的扁平化协同化范式转型,形成信息高效流转、需求快速响应、创新能力充分激发的组织新架构[3]。
二、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困境
(一)管理要素的协同失灵
管理要素协同包括对人员、资金、物质、信息等资源的整理、统筹、调配与融合等多个维度,是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在学校管理这个系统中成功协同、优化整合各类要素。但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师生员工的观念、立场、目标、利益等不同,容易出现协同失灵的问题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缺乏互促性。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由于各自主体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存在差异性,统一协同力度不够,在转型的支持意愿上存在困难,且缺乏数字化素养,难以真正参与转型工作,使得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矛盾冲突,带来破坏性结果。二是缺乏整体性。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初期阶段,基础设施及相关技术并未完全成熟,学校的数字平台和资源过于分散,很难实现资源共享,而且设备技术参数参差不齐,数据壁垒问题严重,缺乏集约高效的技术系统,彼此不能很好地协调和对接,将对转型工作产生不良影响。三是缺乏保障性。数字化转型的每一步都可能伴随巨大的人、财、物的投入,网络、平台、数据、软件、系统、设备及日常运营与管理,每一项对地方政府财政都是巨大考验,且投入产出效益无法估算,学校难以保证资金的投入程度和持续力度,也就难以掌控和平衡分配教学和技术资金比例。四是缺乏均衡性。当前,我国教育均衡短期内无法实现,各省、各地、各校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例如东西部的发展差异, 沿海和内陆的发展差异, 城市和乡村发展差异等,这些不均衡的发展状况和重视程度会造成数字鸿沟和体系差异,不利于全国范围内教育数字化转型工程的推进。
(二)管理流程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学校管理流程难以再造的一种复杂性潜因,表述了以往的经验或成就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阻抗力。面对呼啸而来的数字化转型,习惯、安全感、选择性信息加工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可能会让人产生焦虑和抵制情绪。路径依赖实在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理想选择,主要表现在对人际关系、知识工具以及规则文化的依赖[4]。
数字化转型需要强有力的人际关系支持。不过,目前许多中小学教育管理者和师生员工对教育数字化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相关群体数字素养不足,缺乏具备教育数字化转型经验的技术人才和运营人才,人才培养周期和难度相对较大,教师囿于年龄、知识和经历,在教育教学中存在应用数字技术能力的短板,这些都使得数字化转型在实践中陷入窘境。
知识工具依赖是指在运用知识来认识事物、识别风险时受到制约的一种状态。虽然,洞穴隐喻启示我们知识工具并不完全可靠。但是,人们习惯于遵循早已谙熟的认知实践,踞守在每个纵向精深横向区隔的学科疆界[5]。数字化带来颠覆性的认知革命,将知识压缩编码成“0”和“1”,重构了人类知识的生产方式、表征形态与认知生态环境,让许多人陷入数字化角色焦虑之中,如果不愿意走出舒适圈,难以摆脱惯性依赖,在这种背景下,就难以跟上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和要求,转型工作很难进行下去。
数字化转型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而是要受到学校既有规则和传统的约束。实际上,数字技术的利用程度不得不屈服于有关政策安排和学校的利益分配机制。数字化转型要得到外部环境的支持和获得合法性,就必须依赖这些规则与要求,所谓“入乡随俗”,因为学校的持续发展不是基于效率与效力,而是规避高不确定性,以遵从不变的规则为基础的,所以,遵守规则传统要比学校管理内部实际发生的事情更加重要。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在无形中被消解了。
(三)管理结构的趋同僵化
传统学校管理的运行基础是科层制,最突出特征就是等级化、条块化,习惯命令、指示、控制等强制行政手段,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就是管理结构趋同僵化,难以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支撑,并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 等级化倾向严重。在传统科层制下,由于组织架构设置和职能分工限制,学校校长、中层管理者和基层教师、教辅人员仍然按照等级和专业划分决策权限,导致办事层次重叠、冗员多、组织机构运转效率低下。以办文为例,拟稿、审核、会签、签发、注发牵涉多个部门,人员多,周期长,消耗大,无法真正发挥数字化带来的扁平化管理功能。与此同时,系统平台呈现上报数据多,下传数据少,导致上下级行政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面对具有弥散性和脱域性等特征的各类诉求,平台不能灵活、机动地响应学生的诉求,无法及时阻断叠加交织的各类风险。此外,还会导致“目标置换”问题出现,即学校管理者更加关注组织本身的存续和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而不去关心是否与组织的实际目标相符合[6]。
第二, 条块分割困境。数字化转型单靠学校校长独木难支,需要学校上下齐心合力,协同完成,然而,由于受到以权威为依托的组织封闭、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的严重制约,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许多事务并不能够进行明确的分类,业务重叠模糊,责权利无法厘清,数据壁垒现象长期存在。部门之间协同难度大,成本高,不利于对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统一领导和协调。在推动数字化转型中,各个参与主体打破数据壁垒意愿不强,往往以自身的立场去考虑和分析问题,缺乏全局观和系统观,甚至出现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捆绑学校利益。一些管理者具有多重角色,存在角色模糊、角色错位问题,且由于自身利益或者在人力和能力的压力下,出现推诿扯皮、多元主体缺位等现象,致使管理目标不能达成,问题得不到解决。
三、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方略
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牵涉学校管理要素、管理流程、组织模式等全方位的变革,需要统筹规划、系统推进。为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推动转型。
(一)构建数字化转型协同治理机制
数字化是一个管理命题,数字化转型目标在于优化管理要素的利用效率和管理成效。为了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强化数字化管理主体建设,做好顶层设计,优化要素配置,寻求建立一种合作的理念与关系。
第一,打造数字化转型管理团队。数字化转型首先是管理者的转型,关键取决于管理者数字思维和数字化能力。例如,爱尔兰政府《学校数字战略2027》(Digital Strategy for Schools to 2027)明确提出数字化转型首要是提升数字领导力[7]。一般而言,管理者应该具备以下特质和能力:一是数字化心智模式。管理者要知道如何理解数字化世界,而且知道如何采取数字化行动,懂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二是确立变革愿景。管理者应该让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愿景、使命和责任成为全体教职员工的共识,让学校每一个人都能积极主动地调整配合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战略和策略。三是前瞻性创新精神。管理者需要开放思想,以创新为导向,具有数字化创造能力,能够引领学校应对未来教育趋势变化,并且营造一个创造性解决问题和敢于试错的文化氛围,持续地进行管理创新。
第二,探索政府牵引、学校推进、家庭联动、企业协作、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在政府层面,应注重数字化顶层设计,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将学校数字化转型发展列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安排数字校园专项预算,健全完善经费投入机制。在学校层面,倡导以数字技术赋能学校各项业务管理,推动教育管理专项升级,完善数字校园规章制度。为此,学校还应做好数字化人才储备和教职员工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和数字素养的培训。例如,欧盟《公民数字化能力框架》(European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Gitizens)以培养数字化能力为导向,引导各成员国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家庭层面,应搭建家校数字互通交流平台,支持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共同体。在企业层面,应推动校企深度合作,实现学校和企业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共同解决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智慧环境、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难题。在社会层面,应鼓励数字技术的创新活力,激发管理要素潜能,营造良好的数字教育生态。
第三,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沟通协调机制。在推进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消除学校体制壁垒,打破利益固化藩篱,推动管理要素统筹协调和协同创新,推进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数据平台建设。各方主体应该摈弃偏见,加强沟通,求同存异,树立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扮演好合作伙伴的角色,自觉履行数字化转型的职责义务,敢于主动进行正式积极的信息沟通,整合自身与学校内外部各种能量、信息、技术与资源,让自身发展目标和利益与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二)以数字化技术驱动管理流程再造
数字化转型的突出特征是要求所有要素都数字化,并让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具有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美国《2022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2022 EDUCAUSE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就提出以数字化实现环保节约和流程简化[8]。这种变化要求学校管理者破除传统路径依赖,以网络平台为基础,运用数字技术重塑流程,使管理变得更敏捷、更柔性。流程再造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计划阶段。主要包括组建流程再造队伍、聚焦数字化转型目标、挖掘并分析业务需求、用户需求和功能需求,制定数字化行动计划。管理者应该对学校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汇集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数据资源,打造便民数字基础设施,为教师、家长、学生带来更多价值,满足师生员工、家长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二是行动阶段。这个阶段需要确定流程再造项目,推进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平台建设,明晰领导机构、职能部门、群团组织、社团学会等参与主体职权和职责以及相关业务流程,确认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并进行规范、精简、提速和提效,完成对核心业务的梳理和流程再造。同时,对流程再造过程进行监控和调整。三是评估阶段。主要是对流程再造实施效果的评估。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审,对流程再造和优化各个阶段进行综合分析,对流程再造前和流程再造后进行参照对比,主要从服务效率、时间人力成本、师生及家长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价。四是反思阶段。主要是对流程再造最终结果进行分析、评价行动、纠正不当之处,持续完善并进入下一个循环。
在学校管理流程再造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学校个体、群体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变量因素,从组织行为角度考虑如何克服数字化转型需要面对的组织阻力和个体阻力,以确保数字化转型目标的顺利实现[9]。在努力克服转型阻力时,管理者可以考虑几种策略:一是教育和沟通,通过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帮助他们了解数字化转型的逻辑缘由;二是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个体更容易做出转型决定;三是支持与承诺,管理者可以通过提供大量的支持性措施来减少阻力;四是谈判,通过谈判了解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在适当平衡各方需求的过程中降低阻力。
(三)塑造数字化管理网络结构组织
塑造组织架构是数字化转型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德鲁克认为,网络结构是未来世界新型组织结构的发展方向[10]。在数字化环境下,必须规避趋同僵化风险,塑造具备强灵活性、自适应性的网络结构组织才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数字技术恰好为网络结构组织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的观点,网络结构组织由组织节点、组织网络和组织目标三个部分构成[11]。
在数字化转型中,参与成员或组织都可以被视为组织节点。学校管理者角色必须重新定义,首先是数字化转型的引领者和倡导者,通过数据整合应用以及业务流程持续优化,推动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开展。其他参与成员或组织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交流互动,以保证分布于社会不同空间的节点,实现资源的协调与整合,形成一个具有弹性、扁平化的学校管理自适应社会网络结构。这些组织节点的位置随着学校管理事件特征和应对策略的改变而发生迁移,从而保证整个管理网络的动态适应性。
组织网络是各组织节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组织网络。校内组织网络由学校组织机构、学部、年级组、班级之间纵向和横向关系、师生关系等构成,校外组织网络由学校与政府、学校与非政府组织、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关系等构成。组织网络塑造可以通过构建数字合作平台,整合、共享各类教育教学数字资源,开展基于数据化、智能化、社交化数字平台的校内、校际间交流合作,包括教研研究、教育管理研究、学生自主学习研究、教师培训合作等,从而实现共赢和组织利益最大化。例如,美国佛罗里达洲数字化示范学校奥科伊(Ocoee)中学基于数字技术构建了全域式的数字化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活动,引领并推动教学与学习方式的变革。
组织目标是众多的组织节点在学校管理中沟通交流、彼此协同所要达成的目的,推动各个组织节点相互联系和相互合作,整合各个组织节点的行动,促使学校各个组织节点整体合力的形成,产生涌现效应,实现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和效益提升。塑造组织目标的主要任务是提出一种基于共同合作的战略愿景与使命,制定切实可行的参与规则,推动各个组织节点统一认知、统一行动,开展平等对话与协同合作,激发隐含于组织的多样性要素,促进组织系统内部心智共享。
参考文献:
[1]吴晓松.世界大数据技术进展与发展趋势研究[C]//云南财经大学.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及大数据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16:161-176.
[2]李家明.基于价值链的企业信息链模型构建与管理策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9.
[3]段梦涵.科层化还是扁平化:高校应急管理的行动选择与逻辑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2,20(2):34-40.
[4]李汉林,渠敬东,夏传玲,等.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种拟议的综合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1):94-108+207.
[5]余宏亮.数字时代的知识转型与课程更新[J].课程·教材·教法, 2017(02):18-23.
[6]杨红霞,戴国强,洪艳萍.高效与桎梏的矛盾:科层制下教育政策执行分析——以“营改计划”为例[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7):62-67.
[7]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gital Strategy for Schools to 2027[R/OL]. (2022-04-13)[2022-05-31].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69fb88-digital-strategy-for-schools/.
[8]王萍,王陈欣,赵衢,等.数智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思考——《2022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之解读[J].远程教育杂志,2022,40(3):16-23.
[9]李爱民.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J].现代管理科学, 2006(8):29-32.
[10]李涛.对学习型组织结构形式的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2(09):38-41.
[11]李会琼.技术创新网络节点退出机制研究[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16.
The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Management
LIN Qiugui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frontier issu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ow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solve the current school management dilemma, reshape its ecology, and empow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s. However, the curr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management has encountered problems, such as the failure of coordination of management elements, the dependence of management process paths, and the convergence and rigidity of management structures in practice.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overall planning and systematic promotion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management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ing management process reengineering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haping the digital management network structure organization, so as to help modernize the schoo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nhance i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Keywords: School managem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technique; Reengineer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 姚力宁 校对 郭向和)
原标题:学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方略
来源:《基础教育参考》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稿源:《基础教育参考》
稿源:《基础教育参考》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3-06-16 12:00:00
时间:2023-06-16 12:00:00